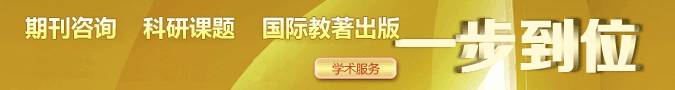文化语境中阐释古代文学研究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张丽红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607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