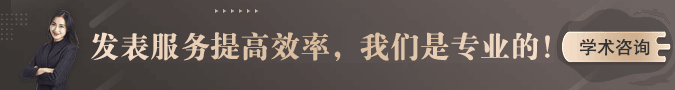编年记作者审美艺术论文
一、秦暴政促成了喜的思想倾向的根本转变
秦统治者是以法家学说为其治国牧民的指导思想的。秦始皇曾在二十八年的琅琊台石刻颂文中批评古代的帝王“法度不明”,标榜自己是“大圣作治,建立法度,显著纲纪”。虽然强调法治并没有错,但秦代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在那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刑罚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盗”,这些“盗”其实是一群被压迫、被剥削而无路可走的农民。失去生计的农民被逼无奈只能铤而走险去“盗”地主的财产,因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击;民不聊生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盗”,而朝廷对“盗”的镇压又越来越残酷血腥。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社会生态下,秦未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绝非偶然。显而易见,秦王朝“严刑峻法”的受害者是农民,秦法不过是统治者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从出土的秦简法律文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刚刚取代奴隶主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是怎样把奴隶制的枷锁换成封建制的桎梏套在农民身上,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3]喜在从政、治狱、从军的经历中亲眼目睹了在秦的强权政治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其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活态度的转变。他从踌躇满志想干一番事业,到对秦政失望而失志颓废,最后选择了自行恬退。喜的经历表明,他17岁便投身社会,为国家效力:先后从政、治狱,到29岁近而立之年时投笔从戎。这说明至少在青年时期,置身于天下一统的强大秦帝国里,他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曾泛起过些许作为楚国遗民后裔的不快,但这并不曾浇灭他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梦想。所以,他从军他乡,独身飘零。然而事与愿违,或许是怀才不遇,或许是现实影响,抑或是性格使然,他始终在底层打着圈圈。如果说从政和治狱难以很快出人头地的话,那么从军在当时是很容易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论功获赏的,但是他却没有。联系到他此时在笔记中极力回避记载有关战事的行为,只能作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他的内心其实是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的,所以他不愿去拼死杀敌建功。于是,他选择了退避。31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此后15年他再无波澜,默默终老。二是记事内容的转变。《编年记》由前期记载国家时政大事到中后期转而以记录作者家事和个人生活经历见闻为主。作者当初写《编年记》的目的,本为记载秦国发生的大事。如在昭王五十三年以前,主要记载秦国发生的重要战役,几乎接连不断;但到昭王五十四年之后,写作的目的变了,对秦国所进行的战争很少有记载了,转而以记自己家事为主。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喜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秦的暴行,不想为其歌功颂德了。境遇的变迁极大地改变他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变了,写作趣旨也随之改变了。三是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的转变。由择要搜集、客观记录、秉笔直书到刻意选择、暗含褒贬、曲笔婉讽,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转变。如《编年记》在昭王五十二年载:“王稽、张禄死”。《编年记》在昭王五十三年中的记述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秦国的内政,而为何独在昭王五十二年记下“王稽、张禄死”?这颇令人玩味。王稽本为秦国的谒者,地位不高,张禄因有王稽推荐才进见昭王,得以相秦,于是转荐王稽为河东守以报恩。后王稽与诸侯通,以叛国罪诛,张禄也受到牵连罢相,王稽与张禄同年亡。[2]27喜唯独在《编年记》中记下此二人之死,恐怕是喜对这两个人的鄙夷不屑、对秦政的曲笔嘲讽吧。这种在字里行间里漫不经心地隐含几分讽刺味道的手法,深得孔子首创的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之妙,其后司马迁在《史记》里也屡屡用到。对某些人和事,他还用一种故意冷落的曲折方式表现自己的憎恶,如对在奠定秦国地位并在统一六国之前有过巨大功绩的白起,《编年记》对其战功及死亡都避而不写,因为正是这个白起攻楚拔郢(公元前278年),使楚国灭亡,而楚国是喜曾经的祖国。此外,也正是这个白起在“长平之战”中残忍地活埋了40万赵国战俘。因此,喜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白起的,所以对其视而不见。这也从侧面表现了他对楚国的怀念之情和对秦灭六国的隐恨。从昭王五十四年起到秦始皇三十年,《编年记》很少再有记录战争和秦国政事的文字,对后来秦灭燕、灭齐更是只字未提。这恐怕和喜的思想意识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联,对于一个自己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满的王朝,他再也无心去记什么秦国大事了。《编年记》在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2年)载:“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据史料记载,此年刚好昌平君反秦,昌文君可能也是位楚公子,本与昌平君同仕于秦,二人还在平嫪毒之乱时一道立过功。其后,昌平君迁居郢陈,起兵反叛,昌文君受其牵连而被秦始皇诛死。[2]35喜为什么要记这一事呢,这只能表明喜的内心是赞成反秦的,对秦始皇株连昌文君是愤恨的,所以在此特记一笔。同时也可以看出喜对楚公子之死的惋惜和伤痛,这不正好是一个楚贵族遗民难以言说的痛楚吗?综上,喜因其楚国贵族后裔的背景,在骨子里有着对秦灭六国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从政、治狱和从军的经历见闻使他对秦的暴政和高压禁锢下人民的痛苦有了越来越真切的感受;同时,自己人生道路的崎岖和灰暗也使他越来越失意和消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这位具有一定知识才能、原本也有雄心壮志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厦轰然坍塌,他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更加强烈,最后终于在政治上站到了秦王朝的对立面,用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秦统治者的不满、抵触和反抗。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和转变,在高压统治和残酷剥削下的秦代社会,尤其是在被秦先后灭掉的原六国子民中具有极大的代表性。
二、从《编年记》看
作者求变求简求新的历史观与审美观再来看看《编年记》的记事内容、风格和文字书写所体现出的历史观与审美艺术观。《编年记》共53简,虽然距今2000多年了,但无论是其记述内容、思想观念、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还是文字书写、字体变化等,较之同时代的官方书写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和全新的风貌,表现出观念更新、记事简约、字迹飘逸的强烈个性和鲜明特色,体现了求变、求简、求新的历史观与审美价值取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1.求变———不满秦政,期待变革
如前所述,喜是楚国贵族后裔,同时又是一个入吏的知识分子。《编年记》写作于“诸侯并作”、“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的时期,对于秦统治者而言,它不仅不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的编史,而且很可能还是“妄语”“妖言”。[4]9幸运的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坑儒”时,作者已逝去三四年了,《编年记》被作者带入了地下,幸免于那堆炙烤文明的大火,才得已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看到这劫后余生的珍贵史料。几百年诸侯割据称雄争霸的混乱政治局面,使秦的统一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但一统天下的战争是激烈、残酷的,统一之后的斗争也是复杂、尖锐的。由于秦统一过程中杀戮太多,破坏太大,加上秦的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致使各种反秦势力长期存在,天下从未太平过。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纵横交织,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这些导致了秦王朝日趋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喜生活的社会背景,也是《编年记》写作的时代背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在《编年记》这一方完全属于个人的小小天地里,用记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秦政的强烈不满和对变革现实的隐隐期待,体现了一种反对暴政、蔑视权贵、同情反抗者和下层民众的进步的历史观。喜对于楚国的灭亡记载最详细。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攻楚,喜的居住地安陆便由楚地一变为秦国南郡的属县,喜由楚人变为秦人。对秦政的不满,加剧了他对故国的怀念,于是他详细地记下了那些耻辱的不堪回首的亡国历史,也悄悄地将自己对眼前这个暴虐的政权及其统治者的强烈厌恶隐含其中。《编年记》中对秦王政持不尊重不避讳的语句颇多。如:秦昭王五十六年,书“正月,速产”;秦始皇十八年,书“正月,恢生”。二处“正”字,均不避讳始皇“政”,而《语书》官方文件中凡“正”皆改为“端”。《编年记》秦始皇二十八年记:“今过安陆”。“今”当指经过安陆的秦始皇,在古代对当朝的圣主应敬称为“今王”,略一“王”字,其蔑视之态昭然若揭。还有,《编年记》中对三代秦王均直言其“死”,如:秦昭王直书“昭死”,秦孝文王书为“立即死”,庄襄王书为“庄王死”。反观喜在记自己的父母之逝时,皆敬书为“公终”、“妪终”,亲亲之情,油然而生,[4]6其憎爱分明跃然简上。对秦王去世所使用的近乎诅咒般的语言,足以表明喜对秦王朝的不敬和愤慨。在秦法淫威下,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解读为喜对秦灭六国、荼毒人民怀有极大的不满和仇恨,希望那个该“死”的王朝和那些同样该“死”的暴君“立即死”,期盼能出现新的社会政治局面,改变当时的一切,强烈的祛旧图新之渴求同样跃然简上。从民本思想看,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历史观。而且,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求变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时代审美观念变革的前奏与先导。
2.求简———刻意省略,记事简约
喜生活的秦苛政时代,严刑峻法如条条枷锁禁锢着人,人们普遍有一种要冲破束缚,过轻松自由的简单生活的愿望。这种“求简”的审美价值取向在《编年记》中可见一斑。《编年记》记事从简,有些地方甚至刻意省略,只书年代不写内容。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编年记》续编对秦王政时期的战争所记寥寥无几。如:“三年,卷军”;“四年,□军”;“十五年,从平阳军”;“十七年,攻韩”;“十八年,攻赵”;等等。凡涉及秦国的军政大事,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用字之简省令人惊叹,甚至略去许多秦人引以为豪的重大事件。在整部《编年记》中,喜并未记载秦国军事上的威武和政治上的强势,对秦国君包括始皇帝不仅没有歌功颂德之词,甚至出现“昭死”、“立即死”等不敬之词。秦王政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即将归于“天下大定”之时,《编年记》却出奇地留下了空白,使人丝毫看不出秦国即将夺取全面胜利的痕迹和普天同庆的喜气。这一再出现的空缺,绝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将它理解为无言的轻蔑和无声的抗议,似乎更切合作者的本意。如前所述,喜是楚人后裔,秦灭六国,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隐痛,不堪回首,故此不书。这足以证明,喜的出身、经历和感受,决定了他是反对恃强凌弱的,更不愿意看到国破家亡的惨象发生。其二,如果说对秦政的用笔简省中包含有政治与情感因素的话,那么,整部《编年记》所显示出的删繁就简的叙事风格,则鲜明强烈地显示了作者对处理复杂题材的一种自觉的审美价值取向:求简。即要言不繁,简洁明了,以简驭繁,以少胜多。这样的例子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几乎用不着列举。如记载私事的:“今元年,喜傅。”“(今)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今)十三年,从军。”……记载时事的:“(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昭王)五十三年,吏谁从军。”“卅七年,□寇刚。”……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编年记》的这种求简倾向,那就是人们在社会制度的强压态势下,内心必然会激发起一种本能的对抗心理和向现实规范相反的方向寻求变革的追求。而且,由繁到简是人们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也是审美观念发展的必然趋势。
3.求新———率意而书,字迹飘逸
书体的变革不单是字体形态的变化,它是与书写者思想艺术观念直接关联的,也是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变革要求密切相关的。战国时期,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到了秦篆的出现,才给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演变做出了总结。从睡虎地出土的两封战国末期的家信来看,民间流传的便不是先秦古文字,而是隶书。由此说明,隶书在当时已经十分成熟,并流行于民间,所谓隶书起于秦代程邀所造也不言自破。《编年记》字体也是隶书,喜在工作之余,提笔在简上记事,所用的书体抑或就是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吧。按说喜作为秦朝官吏,抄写文书包括记事应该是用国家统一文字小篆,而我们在《编年记》中看到的却只是通俗的隶书。[5]在严刑峻法的朝代,作者竟如此大胆,其求新求变之意显于笔端。
作者:陈谷栋 方楚勤 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483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