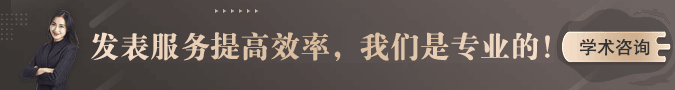癸卯学制与古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的文学教育与癸卯学制颁布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语文教学中与古代文学教育相关的文言文教学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文言文在语言层面上的要求高、难度大,导致实际教学中往往以语言教育为核心,文学教育难以落实。如何在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再次,除了资源配置的平衡、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平衡,还存在古代文学教育与其他文学教育的平衡问题。大学中可以通过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分科来规避中外、古今的冲突,但是中小学只有一门语文课。因此,教材中现代文、文言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安排,也成为一个难题。时至今日,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综上所述,癸卯学制的颁布直接指导了各级官学的古代文学教育,也对民间古代文学教育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看作古代文学教育转型的标志。传统文学教育的政治伦理色彩,被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取代。大的文化教育理念也有向纯文学教育发展的趋势。今天大学古代文学教育、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反复讨论的一些话题,如中西话语冲突的问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仔细考察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对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希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46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