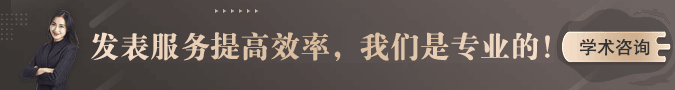现代中古文学研究论文
一、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中古热”
(一)历史、哲学、文学领域中的“中古热”
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化因其时混乱分裂的政局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极端思想,在以“经世致用”“修齐治平”为职志的儒家士人心中始终不被看重。虽然其中也有向儒家思想回归的“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声音,但也依然无补于事,而宋齐梁陈香艳、奢靡的诗风更是被看作亡国之音,使其受到强烈且持久的鄙视与诟病。这样的局面到章太炎时渐露转机。在《五朝学》一文中,章太炎比较汉魏晋唐之得失,痛斥前人责难魏晋之学过当,认为对清谈玄学应当给予重视: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啎,且翼扶之。(……)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与此同时,刘师培对魏晋六朝之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左盦外集》卷九中讲道: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章氏与刘氏对魏晋六朝之学的重新评价可以视为一种思想变化的开端,反映了20世纪初期的学人与他们的前辈有着相当不同的学理思路与历史语境。章氏与刘氏作为先觉者开启了这扇大门,后继者则与他们一道缔造了此时期中古文学研究的热潮。在历史与哲学领域,1901~1929年发表的论文不足90篇,著作10多种;到20世纪30至40年代,论文陡增至600篇,著作有80余种,并分别以陈寅恪的《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为代表。文学领域,公开发表的论文近30篇,论著10余种,并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为代表。
(二)“中古热”出现的原因及其学术价值
为何在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内会出现并形成研究中古的热潮?不少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背景的相似性,认为20世纪初期动荡不安、波诡云谲的政治社会形势与魏晋六朝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那时的学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两段历史两相比附,甚至希望从对魏晋六朝的研究中找到适于当下的救国救民良方。另有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精神的继承性,认为那一历史时期的学人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召唤下,寻求自由与独立,而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勇气、论说及实践,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与精神资源。这些观点都为我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认识,而当时学人的论述言说则为解决该问题进一步提供了直接的参考。闻一多曾这样描述庄学在魏晋的复兴:“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可以说时代背景、时代精神的相似性,知识分子在时代使命、精神追求上的认同感,都是“中古热”形成的动因。作为学人领袖的胡适之下面这番话更从学理的角度重新树立了中古的地位:文化史是一串不断的演变。
古代文化都先经过这一千多年的“中古化”,然后传到近世。不懂得“中古化”的历程与方向,我们决不能了解近世七八百年的中国文化,也决不能了解汉以前的文化。宋明的理学固然不是孔孟的思想,清朝的经学也不能脱离中古思想的气味。汉学家无论回到东汉,或回到西汉,都只是在中古世界里兜圈子。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古思想,方才可望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又可望了解近世思想的重要来历。诸多因素使得中古文学研究在现代突然“热”起来,而这“热”又恰好发生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轫阶段,因此此阶段的中古文学研究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学术史意义。特别是这批学人具有双重的学术背景与思维构架,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功底,又吸收了大量西方学术资源,因此在研究中古文学时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的方法。其独特性在于:首先,不同于古代诗文评传统那种只针对某人或某篇作品的文本式、感悟式研究,能深入具体历史语境做更深层次探析考察;其次,能充分关注文学与文化文本中浸透出的古代文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文本视为语言文字构成的对象;再次,在深入具体历史语境研究与关注文人主体性的基础上,能够与古人平等对话,进行活泼泼的、有生气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具有现代性的学术眼光与思想。因此,总结并反思这批现代学人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以西方文论和研究方法为主的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借鉴和有益补充。
二、语境化——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语境”本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指语言所使用的环境。西方学者一般将语境分为三个范畴:物理语境,即时空;话语语境,即话语世界;原文语境,即上下文。197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约翰•甘勃兹在《语言与语境论集》一书中提出了“使语言语境化”的概念,更加注重语言、言语产生的背景与交流双方的主体心态。20世纪中后期,“语境化”这一概念逐渐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指文学文本、文论思想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包括历史、政治、地域、时代思潮、社会风俗、文人心态等多种因素。但是,“语境化研究并非先勾勒出某种时代的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就万事大吉。语境化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把研究对象看成是在与具体语境的互动中的生成过程,而非居于语境中的已成之物。所谓语境化研究,正是要在复杂的关联中梳理、阐述这一生成过程,揭示其复杂性。语境的真正作用就是在这个生成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令人惊奇的是,现代学者并没有受到西方“语境化”思想的影响,但这一研究路径却正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突出特点。
刘师培首次将中古时段从古代文学中单独抽出进行断代研究,并最早扬弃评点式的研究方法,不再只关注文学文本,而更多地关注文学变迁的历史语境,从政治形势、历史地理背景、学术思潮等多元视角探析中古文学的特点。例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建安文学的分析: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此段阐述文字虽少,内容实多,特别是其中透露出了不同既往的新的方法与视角。首先,欲了解建安文学,必先理解建安时代,这就得需要运用“史”的眼光,梳理从两汉到建安的时代变迁,由此方能明了建安文学与两汉文学的不同特点以及建安文学作为独立单元论述的必要。其次,欲认识建安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要将文学置入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潮的具体语境中探析其生成过程。顺着刘师培的视野和思路,我们看到,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渐兴,并成为士人阶层晋身仕途之主要途径,经学统治了汉代此后的整个学术思想,但由于古文经学囿于章句,今文经学流于谶纬,使得经学的道路趋于窄化,学术思想影响到文风上来,也使得汉末文章偏于繁缛。
“惟东汉以来,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刘师培在列举了汉代杜恕的《请令刺史专民事不典兵疏》与曹魏夏侯玄的《时事议》两篇奏疏后指出:“东汉奏疏,多含蓄不尽之词。魏人奏疏之文,纯尚真实,无不尽之词。”历经汉末大乱,至魏武帝曹操统一中原后,转而崇尚法家刑名之学,提倡通脱力戒繁缛,余风所及,文章也就形成“清峻”风格,即文章简约严明。陶渊明是隐逸诗人的鼻祖,因后世士人对他高尚节操与恬淡气质的持续追慕和歌颂,陶渊明逐渐被建构成一位在田园中过着闲适自在的生活、心境平和的隐逸诗人。但陶渊明的真实生活确如后人所想吗?鲁迅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后来虽然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说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非真实。”那么真实的陶渊明究竟何样,王瑶在鲁迅的基础上从历史语境与个人生活的角度入手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可以说,王瑶对陶渊明的解读体现了语境化研究方法的精到运用。以《饮酒•结庐在人境》一诗为例,这首诗历来被诗家尊为心静淡泊平和自由的典范,但王瑶认为陶渊明的基本思想并未超出他的时代,“‘心远’用《庄子•则阳篇》意,陶诗在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当时一般的潮流,基本的出发点,仍是老庄哲学”。
另外,“采菊”也并非为了玩赏,而是为了服药,为了延年益寿。对此,王瑶做了详尽的考证,证明汉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了采菊并酿制菊花酒以期长寿的事实,且陶诗还有很多表达时光飞驰、人生几何的思想,因此陶渊明采菊以期长寿同样是魏晋士人共有的生活场景。“服药是求生命的相对延长,求神仙是求生命的绝对延长,这是魏晋诗人的普遍思想,所以服药是当时文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陶渊明在思想上是和当时一般文人差不多的,他‘乐久生’,所以他要服食,这就是‘采菊东篱下’的原因。”还有“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亦并非实指,而是用了《诗•小雅•天保》的典故,取长寿的意思,这便与“采菊”构成了共同的情感,都渴望延年益寿。王瑶指出“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自然高雅的意境是被后人建构起来的,并具体论证了这一建构始自苏东坡。东坡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将此诗改成了自己心中所祈愿的意境,却隐没了陶渊明的真实心境。“这种求长寿的想法尽管俗气和可笑,但它却是一种现实的愿望,无宁令人觉得真率和同情;而绝不是一种超尘出俗的静穆,如后来一般名士论客们所赞赏的。”
三、“群体主体性”——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
所谓“群体主体”(或译“集体主体”),是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曾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体与群体相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我”和“你”之外,尚有“我们”这层关系存在,“我们”即是个体群,亦即群体主体。戈德曼认为人类历史由群体主体创造,“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的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理性”。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应当从“个体群”,即“群体主体”的视角出发。“如果不将历史事实和主要的文化创造与某个集体主体相联系,那就不可能理解或研究它们的内涵。”戈德曼认为群体行为相对个体行为,更具备思想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就是群体行为有较为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于群体行为的准确分析更易于把握个人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无疑可以将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视为这一时期的群体主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情趣、生活方式、情感经验,并在相当程度上创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文化。王瑶正是这样做的。如他在分析陶渊明诗歌时所指出的,陶渊明不会也不能脱离他所属之群体,即士族阶层。倘若只将陶渊明做个案分析,则必然会对他的某些言行产生误读,但若将他置入魏晋士族群体之中,我们就会对他整个人获得更加合理化的解释。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将魏晋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早在刘师培那里就已初见端倪。刘氏云: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6]世族①并不是魏晋时期骤然出现的一个群体,实则可上溯至东汉世家大族。而魏晋世族也由此分为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旧族门户由东汉世家大族过渡而来,在魏与西晋时居于高位;新出门户则是由际遇而升迁,在东晋时期尤为显著,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有一定影响力的世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也都具有相当实力与显著特征。陈寅恪提出,东汉末年之乱,使得全国文化学术散落于各地名都大邑,而被地方的豪门大族所承继。“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因此,魏晋是一个学术文化家族化的时期,居处要职的政治身份与一定的经济实力,保障着世家大族的学术文化首领地位。出身低微的寒门读书人,可以通过入仕而逐渐壮大本家族,反过来,有些豪强虽在政治经济上称霸一方,但若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则地位难以持久。学术家族化,使得世家大族子弟在年少之时就可享受到各种学术资源,并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等级制度,进一步促使学术文化在“上品”贵族之间无障碍地流通,使得世家大族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贵族,更是精神文化上的贵族。以陈郡谢氏为例:(谢)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涉猎文义,博赡多通,时人以方杨德祖,微将不及。晦闻犹以为恨。帝深加爱赏,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谢晦因“涉猎文义,博赡多通”而被刘裕所赏识,甚至于“内外要任悉委之”,足见学术文化的修养对于士人地位的重要性。同样,谢混也因文采出众而伴随帝王左右。谢晦、谢混的被赏识与重用,足可使得谢家成为名门望族,而这便是世家大族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学术文化的修养是可以传承的,用以维持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地位。陈郡谢氏中不乏这样出众的人才,据《南史》记载:(谢)瞻字宣远,(……)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叹异。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谢裕)子微字玄度,美风采,好学善属文,位兼中书舍人。(……)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梁武帝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览焉。(谢)朓字玄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为齐随王子隆镇西功曹,转文学。(……)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谢方明)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可以说,陈郡谢氏之所以能够成为江左以来的世家大族,绝不是仅凭一两个人的能力而为。由于他们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几乎代代都会出现几个在当世具有绝顶风采与文采之人,且因为家族化的教育可以自幼年始,因此他们甚至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誉满天下。这也正如刘师培所云:“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
四、“体验”——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
本文所论之“体验”,即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论之“了解之同情”,近于朱子所谓“涵泳”,亦即我们所说的“体验”: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是不以今日之眼光、要求去苛求古人,对古人及其文本能够抱着同情的态度去理解,也便是一种尊重古人及其思想的平等对话精神。“所谓‘对话’,就是以平等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对待所要言说的对象,把对象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独立性的发言人,而不是死的文本或可以随意解读的文字。”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大家如刘师培、鲁迅、王瑶诸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就能够对魏晋时人持此“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此,他们的观察往往入木三分,提出的观点亦多属人所未发,在这里,设身处地的“体验”居于核心位置。19世纪末期,选学派与桐城派之争甚盛,表面上看是骈散不同之论,实质上则是学术上的汉学家与古文家之争。属于选学派的刘师培对骈文推崇备至,这与他受乡贤阮元的影响以及扬州学派与《昭明文选》之关系有关,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则反映刘氏对骈文的一种认同与尊重,他曾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在他看来,骈文、韵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不应该被忽视和抛弃,骈文有着独特的美文性质,不能简单地否定与废弃。事实确实如此,骈文并不是死掉的文字,从魏晋时人的骈文韵律中依旧可以读出他们的文采与巧思。后人对骈文的诟病,多集中在批评其虚浮无辞,但刘师培通过对桓范《世要论•赞象篇》与《铭诔篇》等进行研究后指出,早在东汉之时,“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因此,他对骈文的优劣得失做了中肯的评断,认为“当时文学之得失,亦以见文章各体,由质趋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者渐矣”。
显然刘氏的见解不是由概念得来,而是对文章进行体验与涵泳的产物。陈寅恪所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说法是在讲一种以体验为核心的读书方法,这与朱子“涵泳”一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涵,沉也。扬雄《方言》曰:‘南楚谓沉为涵。’泳,潜行也”。可知涵泳本意为水中潜行。宋儒则借涵泳一词来表示一种重要的为学方法。朱子谓: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肠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泳,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朱熹将涵泳视为一种为学的方法,且不是一般的只求知识或理解书中之意的方法,而是深入书中进行体味、体悟、体察与体认,进而达到一种心灵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获得愉悦与享受。倘若不只将古人或古代文本仅仅看作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是能涵泳其间,走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求得与他们心灵上的灵犀相通,便是所谓“神游冥想”的境界了。刘勰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处之“神”指作文构思之灵明一点之性,“物”则为作家眼中所见之物,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刘勰“神思”这一妙用,将“神”延伸为涵泳古人心灵之间的那一点灵明,将“物”扩展为古人或古代文本,而做一番庄周梦蝶之美梦,也必定有其妙处。刘勰所论也不离“体验”二字。
五、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及其当下意义
现代学者的中古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具体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之外,在方法论上还有两点重要启示:
(一)充分尊重所研究之对象
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深深根植于中古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其取径和特色皆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中来,而非凭空杜撰。例如语境化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是一个巨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酝酿出的历史精神、政治诉求、生活习俗、士人心态以及文化艺术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人的逸闻趣事,很多士人的行为言语在今天看来皆属非常可怪之事,然而这些在当时又是普遍存在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语境化的研究去理解和把握时人的思想与心态。又如群体性研究。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是中古时期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一个阶层。从士人个体的存在形态着眼,魏晋士人大都分属于各个世家大族,几乎每一位士人背后都立着一个大的家族集团;从士人群体的历史属性着眼,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这一整体又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有特殊地位的“士”阶层。政治地位的保证与经济条件的优厚,使得魏晋世族在文化上形成了独特的趣味,在哲思上充满老庄情怀,在文学上则洋溢着对玄远情趣的追求。嵇康“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的人生情趣,陶渊明的恬淡心境都是最好的例证。再进一层,魏晋时期士阶层的政治地位、文化趣味、社会风尚、文人心态以及学术旨趣虽然在不同朝代会有所不同,但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并未断裂。很多士人一生就经历了多个政权交替,如刘勰,他一生经历了宋齐梁陈整个南朝时期,将他的一生割裂开来置入不同的朝代来研究显然偏颇,而必须给以整体性的关照。更重要的是,这种士人特别是他的家族可以凌驾朝代的更迭而独立存在和长期延续的现象,使魏晋时期的精神血脉、文化趣味、文人心态呈现出一种相通性与传承性,因此,群体性研究就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对所研究对象的充分了解与尊重,使得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使得中古文学重新获得生机与魅力。在今天的文学、文论研究中,若也能对所研究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与尊重,或许在理论和方法上就不会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了。
(二)在中西会通中有所创获
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位大家之所以能够建立一套大异于过去的研究方法,与他们的学术视野较前人广阔得多有关。他们既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又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的特殊时代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与方法,从而具有了现代性的学术视野与学术眼光,这是前人所不能及的,这也正是现代学人能够开创现代性学术的关键所在。学通中西的吴宓就道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卓识:“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可以说,刘师培、鲁迅、王瑶等现代中古文学研究者正是如此这般的。成长于扬州学派家学影响之下的刘师培于音韵、训诂、经史、文章无一不精,具备传统学术的根柢与素养。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看出,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书所引的文献资料之丰富以及逻辑之严密,就是直观的证明。但他亦不排斥西方的思想,反而积极接纳之,并尽快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例如他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就首次使用地理的视角来做说明。就学术方法而论,在近代科学思潮中,中国文学研究逐渐走出传统的评点、感悟式研究方法,开始注重学术方法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既有传统性方法的承继,又有西方新思想、新方法的尝试。兼容并包地吸收着中西双方的学理营养,产生了现代中古文学的研究方法。当下的文学文论研究,或许也应该在中西思想的浪潮中打造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既不抱残守缺,也不盲目崇拜,在中西学术营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基点,产生新的研究视野。
作者:史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428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