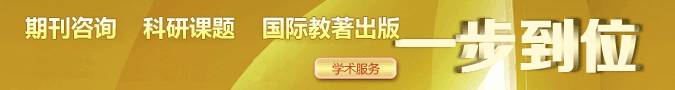探究新时期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嬗变
一、文学表现方式的嬗变: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化
深度写作、宏大叙事几成中国文学的特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人们带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文学的仪式意义渐被消解,文学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之一,深度写作的给力环境不复存在,文学写作面临着多种选择,可以坚守,也可以寻找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同构,因而出现了文学的多方面嬗变。新时期文学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伴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高蹈于政治化语境,其内容与时代主旋律互动同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消费主义成为时尚,大众传媒文化颠覆了经典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者再难守持原有的深度模式,需要对接受环境密切对接,于是引发了文学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从深度模式转到平面化,作品的内蕴与深度让位于表层材料的真实与新鲜。形而下的生活具象被强调,形而上的艺术与哲学精神被丢弃疏离,走上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传统相悖的路,作品不再追求耐人寻味的深沉和深刻、作家也不再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坚毅和执著。文学的这种转型毫无疑问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观的成果,后现代主义作为大众文化的精神源,视文学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无需深度,无需阐释,只要平面可复制、易传播即可。法国摄影现实主义就要求作品像摄影一样复制生活,高度逼真而无需深度,美国美学家苏珊•桑格塔提出文学作品“反对解释”。她说,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来解释一部作品,她认为文学的刺激性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在她看来,但丁等文学大师“为使艺术作品能够在不同层面上被体验而对艺术作品进行谋篇布局,想必是一种革命性、创造性的举措。现在它不再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了。它只不过强化了作为现代生活主要苦恼的那种冗余原则。
当然,苏珊•桑格塔的美学思想也在某种意义上有其不乏深刻的内涵。但她明确反对文学的“深度模式”,是对传统经典文学的颠覆。文学创作有依据地从原来的深度模式追求转变为平面化处理。著名作家王蒙就曾感叹过,现在追求发行量,追求票房价值,追求眼球效应,文学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了。以至于《知音》、《故事会》就是人们理解的文学。在前传媒时代,文学还是守持传统的表达方式,维持高贵的姿态,追求对人的情感表达的精致性、深刻性,竭力追求深度模式,有四种形态: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事物的核心在本质深处,文学要着力写出事物本质。二是精神分析学的隐抑论,认为事物分为明显与隐含两个层面,文学追求的“隐含”的深度模式。三是存在主义的非确实性与确实性,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确实性。四是符号论的能指与所指,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所指”。这种守持在大众传媒时代被分化,被弱化,虽然仍有部分作家坚守,但在消费主义时尚影响与大众传媒的解构下,更多的是作家不执着对“生活深度”深入体验与提炼,而是欣喜于大众媒体的现场效应,独钟于简单的“生活平面”,对可复制充满快感。作家不再以作品深远影响人的心灵为荣,而是以作品发行量为陶醉。他们同意接受以现实生活现象为题材的文学,但动摇了文学越过生活现象而抽取到它的本质的观念。他们只相信眼见的真实,即生活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而形成的感受和印象本身,不再信奉甚至不承认在生活现象背后存在某种超出个人感受和体验的理性的真实。随着大众传媒的无限扩张,文学写作不再可能以精神(情感)的精致表达来实现自己的独创性,而是强调了自身在一场规模巨大的传播活动中的观赏性价值。总体上,文学“快餐”取代了精神盛宴,新媒体写作,让全民进入作家时代,传统的纸质文学,新生的电视文学,广播文学,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网络文学,甚至手机短信也成了文学形式。文学俯身于传媒,确实带来文学的惊人数量,文学几乎无处不在,不过,留得下来的真正具有文学品格又有多少呢?文学面临广泛质疑,作家含金量由此缩水。大众传媒解构了文学的神圣,解放了作家的自由,作家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压力,却也让作家们过于陶醉自我,满足“我见”,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一切。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都市”文学和“身体写作”等,把以往由于意识形态和落后文化影响而忽略了的一部分生活、情感、细节重新纳入艺术视野,并无拘施以浓墨重彩,为人们提供现实的新的文化景观或生存景观,看上去如同现实主义,但由于抽空了内涵,消解了深度,只依了现实主义的形式,浮光撩影,实则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无论是“新写实”的原生态,“新体验”的现象追踪和体验,都市文学的“欲望化”表现,看上去很美,但都没有形成新的对于历史人生、文化意识形态的穿透力,其所复现的现实,没有越出个人日常经验范畴,因而只能随风飘逝。客观地讲,文学内容表现的这种转型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把定位固定于深层模式,以宏大叙事、深刻意义作为唯一指归,也狭隘了文学意涵,文学应该有全方位的自由,以前的文学也过于地强化了深度功能,不过,矫枉过正,一味的平面化,放弃文学的核心品格,无异于自我裁军,自毁文学。尤其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因这种文学创作回避或者丧失对生活的穿透而调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对接,而是过分迷恋凌乱偶然的生活现象的堆积所带来的浅层快感,不再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说,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解构,走向了形而下的具象的写真,放弃了通向人的精神真实的路。
二、文学功能的嬗变:从教化到娱乐化
与放弃深度模式,选择平面化相适应,文学作品的功能也从从教化转型为娱乐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在“眼球”,目标在利润,这就必然催生以市场为主体的大众文艺的崛起,娱乐化成为文学的功能特征,“文以载道”被解构,文学回到散漫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实践表明,文学始终在服务大众与寻找自我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纯文学逐渐式微,日趋贫困,而另一方面大众文艺则遍野蔓生,随物赋形,娱乐、休闲与文艺结合,一切传媒手段皆参与文艺制作,网络文艺、手机文艺、视听文艺、无厘头的戏说穿越“恶搞”文艺以及种种名目繁多的、具有广泛大众性和强烈行动感的文艺应运而生,文艺消费主义蔚成大观。文学从来没有这么乱花迷人眼,这类文学直接以娱乐为目的,娱乐大众也自娱。文学文艺成了“快餐”,当然也满足了最大范围的文学大众的需要,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坚持传统的教化功能的高雅、凝思、无怪力乱神的、用于陶冶和文化积淀的文艺,在消费时尚与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下也艰难得更新,也在追求娱乐元素的强化,追求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追求一定的消费接受。比如为了好看,出现了戏剧、歌舞、杂技和现代舞台科技多样式的渗透组合,出现了音乐剧、人偶剧、杂技芭蕾、小剧场艺术等艺术形态,香港用3D技术拍摄了肉欲撩人的“肉蒲团”,而北京又弄了芭蕾“肉蒲团”,娱乐几至无边界。文艺的属性是多元的,娱乐性是其题中之义。传统文学强化教化,坚持文学以思考、深邃,载道于主流价值,作用于人的心灵为目的,虽然也强调“寓教于乐”,但是,娱乐不是目的。文学总有一种使命感,厚重感,深远感,作用于读者深层心理。文学希望接受者通过文学接受体会到责任、价值。文学的这种定位抓住了文学的核心价值,不过,娱乐性也因此往往被忽视,或者说为了核心价值的表现而有所牺牲。这样,文学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就可能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文学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更新,要与时代同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消费时代,文学不得不从人生导师变为消费对象,下圣坛而与众生为伍。不过,这种调整也不应否定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教化目的,相反,娱乐化应该有所克制,注意“度”,一味市场化,迎合读者的肤浅接受心理,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意义。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消费主义渗透人的全部生活领域,文学市场化亦成趋势,文艺创作变成了地道的文学生产,文学创作的专业术语已简化到与市场生产术语同构,艺术构思、典型化、艺术风格等专业术语被操作方法、运营模式、编辑方针等代替,文学娱乐价值的片面强调和市场化运作将文学导向庸俗与浅薄。文学书刊出版,市场收益成了最大的考量。绝少把文学的意义放在首位,而主要是看它的消费市场,有的甚至采用作者包销形式,虚构消费市场,把文学彻底沦为商品。曾经神圣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一般商品的制造,曾经劝人读书促人成才的古训“开卷有益”在今天已不再是真理,复杂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简单的对发行量(读者群)的追逐,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大众文化时代,市场经济削平了审美的深度追求,追求最大的通约项,即大众娱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覆盖各式各异兴趣和观点以及利益要求的是娱乐,产品是最易畅销的公共产品。于是,文学市场成了大众消费市场,一方面,纯娱乐消闲的栏目和内容广泛盛行,另一方面,非娱乐性的内容,也想方设法注入娱乐因素,文学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泛娱乐化。娱乐至上,主流价值缺失。今天,重新过分强调文学教化功能而拒斥娱乐化或许以为不可,但是辩证地予以取舍似乎不可少,必须纠正娱乐过分追求形而下的庸俗与浅薄,让娱乐回归文化愉悦大众的本位,夯实心灵书写的文化质感,填补价值缺失的人文精神。应该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吸取养分,学会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净化、对正义的诉求,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理性回归,让内心真正变得强大,让心灵真正崛起,走上娱乐的正路。“文学市场既不可能驱逐大众化的通俗作品,也不能一窝蜂地走娱乐化之路:文学要张扬其娱乐功能的本性,但文学的教化功能也依然应是不变的追求。”
三、文学表现形式:从内在美到外在美
大众传播的特质是当下性与即时性,文艺的特质则是对心灵美的重视,注重精神层面的深刻揭示。大众传媒时代必然对文艺的的这种特质构成冲击,促使文艺向眼睛、耳朵的美感和快感的转向,赏心被悦目、悦耳替代。读图时代的到来,更是开足了浅层感官的功能,“好看”成了时尚,成了文艺的基本标准。审美被物化,被悉心经营和强化的色彩、构图、光影等可视的物象所替代。“诗意的栖居”不再是精神的栖居,而是对官能的诱惑。一方面,文艺创作强化表层的形象元素,力图声光影的外在美,一如张艺谋电影的炫丽斑斓,一如一些作家在篇名上的花里胡哨,文艺作品将表层“好看”作了卖点;另一方面,文艺批量生产与不重内容而重外包装,精装、镶金,在包装上下足功夫,整个一绣花枕头。在“好看”的追逐中,文艺刊物纷纷化妆打扮,粉墨登场,各种文艺期刊为之改版调整,《北京文学》明确推出“好看小说”并热情推销:“好看小说就是好看小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看,篇篇好看,篇篇耐读,它能使你不忍释卷,恨不管一口气读完,它也能让你在床前灯下细细品尝,久久回味……”其实,“好看”是好看,“久久回味”未必,“好看”一词正式成为文学关键词。文学变成了文学市场,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好看”本是迎合市场而诞生,缺乏科学的意涵,正如作家毕淑敏所指出的,是个“简陋的接受美学命题”,“判决权”全在读者手里,“读者觉得好看,它就好看,读者觉得不好看,它就不好看”。更有甚者为了上视像媒体,把暴力色情作为“好看”卖点。如泛滥的“肉蒲团”等,“好看”也就标志着读者被确立为真正的“上帝”,文学发生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重新确立作品价值评判系统的由“圈里”到“圈外”的根本性“位移”。不可否认,“好看”显示了文学对读者权利的重新尊重,切合了接受美学原理,尤其是对以前文学一味讲究宏大叙事,讲究服务于“道”等外在功利目的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除了不绝于耳的被官方容忍的“票房价值”数据满天飞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国家三大图书奖励十分明显地将发行量列为为参评条件中,要求参评图书在申报材料中注明印数,强调为读者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其逻辑似乎“好看”等同于“好卖”,进而等同于“好书”,这对文学极具潜在危害性。“可读性”诚然重要,票房价值也不是坏事,正如一些专家所断言的:“艺术向世俗的无限妥协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想像力的萎缩,审美深度的削平。作家为了保持作品长久的吸引力———“好看”,往往采取的捷径是“经验化”写作,而读者也习惯了用已有的“好看”重新唤起新的阅读期待。”这就带来了缺乏创新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或相互模仿,“作家沉浸于自己的作品好看、有趣、富于刺激性和震惊效果,大多显示出“同族化”的类型特征。不少作品都只是同一模特改头换面后的时装表演,一些段落只不过是人物姓名改动了一下,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进程和消费主义时尚的兴盛,文学艺术紧紧与大众传媒关联,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但过分追捧传媒效应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作品的水准下降、审美价值的降低,最终导致经典性作品的缺失,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诚如斯言“文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纠葛盘根错节,端繁绪杂,迄今为仍是文艺研究中尚未彻底厘清的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毛正天 史红玲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46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