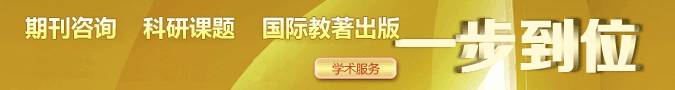浅议家庭教育对张溥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励志教育:明确的学习动机是勤学的力量之源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张溥出身于苏州太仓一位小生产者的家庭。陆世仪《复社纪略》称张溥之父为“太学生翼之”,程穆衡则称其以放高利贷为生。他曾在《先考虚宇府君行略》中记述说:“王父先世贫,及身稍振,有市廛一区,秔田三顷,析而为三。先人业不及中人……雅非所长。”(简称《行略》)其父张翼之因为乐善好施,曾一次性资助外家的远房亲戚“千金”,又曾多次陷入官司之中,故积蓄恐怕不会很多。张溥为后世所熟知的“七录斋”,也并不是什么深宅大院,而是乡间一所小房子。杨彝曾经记载:“世所称七录斋仅两楹,受先坐卧以之,客集则归侍母。”张采《庶常天如张公行状》(简称《行状》)则直接称七录斋为“陋室”,其云:“(张溥)十五丧父,同金母出居西郭,颜一陋室曰‘七录斋’。”要之,七录斋不过两间房子,张采(受先)同学其中,遇有客人来,就没有他待的地方了。《行状》继续说,张溥在父亲去世前后,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甚至连买书的钱都没有,只好自己动手抄写。其云:“(溥)私习举子业,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买书钱。盖虚宇公虽素封,子多弗及周,则金孺人?麻绩祍佐公。日夜取成书,断章手录。”这些记载表明张溥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或文化世家,他所受的励志教育也并非高门华胄与生俱来的自豪感。伯父(张辅之)虽成进士,位居南京工部尚书,但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荣誉感,反而带来了伤害。张溥之所以刻苦自励从而拥有成功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而这种动机正是来自家庭所受的屈辱。陆世仪《复社纪略》对此有所涉及,他说:“翼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翼之。溥洒血书壁曰:‘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奴闻而笑曰:‘塌蒲屦儿何能为!’溥饮泣,乃刻苦读书,无分昼夜。”甚至他以翰林院庶吉士乡居期间“读书仍若经生,无间寒暑”。张溥本人对此记载更为详尽。前引《行略》说:“私念先君少历忧患,老而弥酷,日延师傅,躬教挞以望子之有成。”在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中,清楚地记述了感于父亲所受“忧患”而刻苦攻读求得科举功名的初衷。他还说:“然先君摧辱之时,子虽多,大者二十余岁,少者仅八九岁,无一人奋声激昂,稍借爵位气势拔先君于祸患。”家庭中的难言之隐,伯父一家主奴的飞扬跋扈,极大地激发了张溥欲借功名势位以扬眉吐气的决心,因而刻苦学作八股文。如他在《张露生师稿序》中说:“每念先人教子勤苦,夜半起,篝灯辄成三四义。”这样一种励志教育,思想格调固然显得不是很高,但却是张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最能从骨子里激发他内心的奋斗精神,他因此而不断强化的学习劲头,始终没有衰减。张溥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治学目标、高远的治学旨趣,使他能够超越个人得失,将自己的志向与社会需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了相当强烈的使命感。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升华了励志教育的境界,是一般泛泛而谈的空洞说教所不能比拟的。张溥十九岁得补弟子员,成为秀才,可是其学术旨趣与当时科举考试的要求相违背。因为“嗜古”的原因而好用难字,语句不通,以致“试皆下等”。当他于天启四年冬天(公元1624年)走出七录斋参与结应社活动,转变学术旨趣与文风之后,才能做到“距结社不去三月,试皆上等”,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凤基会业序》)。他在县学有如此迅速的进步,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天启七年的乡试资格,却在这年落榜了。即使遭遇挫折,仍然有所收获。随着次年的选贡入京,他游历太学,极大地开拓了心胸与眼界,扩充了自信心,进一步明确了学术目标。甚至在京城举行成均大会,公开提出了“砭俗学,尊遗经”的学术纲领,并“与燕、赵、鲁、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以至于程穆衡在《娄东耆旧传•张溥》中称他“为诸生时,即以道学文章转移天下为己任”。张溥在家庭教育中获得了学习的动力,不仅仅来自观念的教导,更多带有一种生命体验,因而是深刻的、持久的。当我们回顾他的成长历程时,仍然不能不注意到教师和家长的直接教诲与督促。
二、师生授受:赏识与督促激发了张溥的自信心
教师和父母在孩子学习的初期阶段无疑负有指导与引领的作用。首先,教师的专业水准与教学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效果。张溥的蒙师张露生虽非极一时之选,但也是地方上屈指可数的名师,崇祯七年举人。前引《行略》称“先君待朋友诚,尤敬事名师”。而教师对学生的赏识,正如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所揭示的,最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与学习动力。张露生对张溥无疑具有知遇之恩,正是老师的赏识极大地提升了其对学习的兴趣与信心。《张露生师稿序》记载了这一段师友渊源:“予年十一,从先生学文字。时粗解把笔,先生谓为可教,时称述于先子。”张采《行状》记载:“(溥)长而语采:‘我自遇露生张师,始获黄童誉。’”“黄童”指汉朝时期的黄香,时称“江夏黄香,天下无双”。张溥是教师眼里天下无双的“黄童”,这样的称许对他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成年后还向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津津乐道。其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模仿的最重要对象,在家庭教育中负有关键责任。张溥曾经为自己父亲的渊博而骄傲,在《行略》中曾深情地回忆道:“先君警悟,善读书……二十一史及《通鉴纲目》皆手评录,间与伯兄征斗古事,往往得胜,覆茶噱喜。”张溥后来刊刻了大量史书,并遍论明朝以前的所有皇帝和明朝以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事件,写下了六七百篇史论,或许受到过父亲的影响。与此相联系,家长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孩子的学习,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困惑。在这一点上,其父亲的做法虽然有点“关心过度”,但是效果很好。《行略》说:“(先父)晚年困顿,益锐身教子。一宅不能容,则分二宅馆给,惧礼不至,日往来简束其间,督诸子读书,夜漏不尽不入内。”父亲为了教育他兄弟十人,在家里设了两个馆,一方面加强与教师的联系,一方面督促诸子读书,直到“漏尽”始睡。这对他的成长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张采《行状》即记载道:“(张溥)从师受读,日可受数千言。暮反,至虚宇公所,或呼问今日何书,琅琅诵不休。虚宇公绝怜爱。”张翼之每天检查背书的情况,以及“绝怜爱”的情感反馈,无疑会促进他完成功课的积极性。《张露生师稿序》反复称述父亲督促兄弟们的学习说:“先子益内喜,督群兄弟加严,蚤夜视先生起居。”“先子持家政劳苦,晚必同先生饮食。”“先子年高,晚岁重困,望儿子成学甚亟。”“先子置榻壁间,倦或少憩,闻书声即起,喜不成寐,纵观诸子课竟,然后就内寝。自是率以为常。”张翼之对孩子们学习的投入,换来了令人欣慰的结果。张溥在翰林院写《行略》时,他们兄弟十人全部成“州庠生”、“州廪生”或“州增广生”,其中张涟是太学生,张浚中了癸酉副榜,张王治中了庚午副榜,入清后还中了进士。甚至连他侄子辈,也有好几人成了秀才。除了教师赏识和家长参与,培养适当的学习方法同样重要。万斯同《明史稿》记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张溥以“七录七焚”为标志的朗诵与抄写并举的学习方法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附带指出,有论者说张溥之所以养成抄书的习惯,是因为他“脑子笨”,是为了强化记忆而采用的笨办法。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有很多材料证明张溥小时候聪颖异常。张采《行状》称“公六七岁,奇慧,不逐童戏”,陈子龙《张天如先生文集序》则称“亡友张天如先生有敦敏之姿,宏远之量,英骏之才,该博之学”,邹漪《启祯野乘》说他“儿时奇慧,好学如成人。日读书数千言”,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张溥》也称其“禀资异敏,视日不瞬”。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被蒙师誉为“天下无双的黄香”。家庭教师和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如果能进一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琢磨,不断交流,就有可能真正使学问有成。
三、社会教育:社友切磋开阔了眼界和胸襟
中国古代教育家非常重视同学间的交流与切磋对于提高认识能力与理解能力的重要性。《礼记•学记》上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张溥正是通过与朋友共学,深受启发,不断明确学习目标,直至最终提出“兴复古学”与“务为有用”的复社纲领。父亲去世之时,张溥的朋友并不多,曾云“而予当时之友惟一方旭”。赵方旭在他兄长张质先家坐馆,两人时常切磋学问当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与张采的交往与共学,是取得学术上长足进步的重要因素。张采《祭天如兄文》对此有深情的回忆。其云:“忆弟友兄,始庚申岁(公元1620年)。及癸亥,延我七录斋。逮丁卯,凡五年中,兄每辰出,夜分或过子刻入。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高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大理。”这种切磋,一直保持到张溥临死前。其时,两人仍旧“至则谈平生,考古今,亦何减七录斋时”。在七录斋同学的管君售,也是最初共订应社约的六个人之一。张溥说:“六年以前,风雨寒暑,予与受先、君售同之,逾年而君售别去,一室之内,出入依倚惟两人耳。”又,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夏之交,张溥始与同里以《周易》为专经的龙重孺、曹穉涛、王家颖、何南春、蔡伸等几位生员结“易社”,他们“一社又皆业《易》,《四书》经文无不共题”,这几人也多成进士,为复社的重要成员。而且,同社之人通过同题共作的方式较长量短,共同研讨四书文及以《周易》为内容的八股文的写作,为以后结应社时形成明确的治学目标与“五经分治”的治学方法提供了实践经验。结应社无疑是张溥走向学术成功的重要契机。天启甲子(公元1624年)冬天,张溥与张采共同前往常熟访问杨彝,“因遂定应社约”,为他开启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同社杨彝对张溥因为盲目嗜古,学问过于驳杂,又好写难字,文不成句提出批评,引导张溥转向经学,“余不许,约以通经,诸子即无不经学”(《凤基会业序》)。不久,张溥与张采共同造访金沙周钟,最终完成了学术目标与科举成绩的转变。从金沙回来后,张溥“更尚经史,试乃冠军”(《复社纪略》)。由一味嗜古转向经史之学,不仅改变了张溥在科举之路上的窘况,同时为后来提出复社的学术目标奠定了基础。这都是在与社友切磋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张溥后来曾经回忆在五经应社中与杨彝一道学习《诗经》的往事与体会说:“子常好聚书,先以经为本,诸经书充户牗,分别治之以已……余时左右窃听,间有发明。”更重要的是,张溥通过与同道的切磋交流,摸索出了有效的学习方法。他在为五经应社所作的社序中,将杨彝的宗经主张演绎成如何治经的方法,提出“五经分治”,并进而提出“通论六经”。正是在这一段时期确立了他“志为大儒”的人生追求。邹漪在《启祯野乘》中写道:“十九补诸生,同邑吴伟业从公受《易》,相期以天下事,志为大儒,且不欲以科名让人。”按照一般的看法,教育有三种类型,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除学校和家庭以外的其他任何场所里所进行的一切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都是社会教育。可以说,张溥与社友间的切磋交流,是一种自发的教育,是一种自我教育,同样也属于社会教育。这种社会教育不仅对张溥的科举生涯和学术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成为复社科举人才辈出和明清之际学术转向的重要原因。
四、刻苦自励:只有内化为自觉行动的学习行为才最有效
无论教师,还是家长和同学,都只是外部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习主体的学习态度和努力程度。张溥作为教育的成功案例,不仅能给广大家长和教师如何指导孩子学习提供一定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刻苦自励、孜孜不倦的勤奋学习的榜样。以下摘取几则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刻苦勤学在张溥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张溥勤学故事中流传最广的一则当属“七录七焚”的故事:“用是右手握管处,指掌咸成茧,数日辄割去。冬月手皲,日沃汤数次。其勤学若是。后名其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明史稿》)张采《行状》记载了一些张溥勤学的例子。有一次,他边吃粽子边看书,由于看书入了神,在蘸糖时蘸到了墨汁,还是照常把粽子放到口中,嘴唇和脸上都粘满了墨汁。文章说:“然公同余读书时,见公得粽设饧,误渍墨,口辅尽黑。余笑,公终不觉。”还有一个冬天,两人读书至深夜,灯油尽了,灯光灭了,他们看到雪光映到窗户之上如同白天,就以为是天亮了。到院子里一看,原来已经下了足足一尺深的雪。文章中说:“夜深灯尽,窗照如白日,疑遂天明。视庭中,则雪深一尺。呼童子,鼾睡。”蘸着墨汁吃粽子浑然不觉,深夜门外下了一尺深的雪也毫无觉察,可见其学习起来是何等专注!张溥一生始终保持着这种刻苦自励、勤奋学习的精神,在治学、教育、政治活动等方面也具有同样的作风。张采记载他起早贪黑治学的情景说:“读书日高起,漏下四鼓息。起坐书舍,呼侍史缮录,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辈不给。”(《行状》)“凡经、史之言日不去目,漏过子刻尤极庄敬”(《天如稿序》)。黄宗羲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则张溥嗜学的故事,他在《思旧录•张天如》条写道:“天如好读书,天姿明敏。闻某家有藏书,夜与余提灯往而观之。”张溥在临殁的那年初,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据他的弟子董说在《祭张夫子文》中提到,辛未正月(公元1641年),张溥仍然彻夜工作:“说今年正月见夫子时,说病新起死伍也。夫子曰:‘噫,甚惫。’为惕然惧久之。而说之视夫子方强饭,能达旦不寐,皆上寿之相。”董说认为的“上寿之相”,陈子龙则从另一个角度记载了张溥始终保持教书育人的热情说:“天如病笃,犹与门人讲《易》。已,谢门人曰:‘日月甚明,我将行矣。’乃逝。”此外,张溥至死仍然坚持他的政治理想,临死前十七天,与张采交流对复社社事活动的看法,张采劝他结庐隐居说:“拟购旁隙地为潜息所,兄抱仆被,两人寒窗拥炉,仍修旧日静业。”张溥则不然,而不愿意放弃“志在担荷”的初衷(《祭天如兄文》),直至去世。从张溥的身上可以看出,自身的刻苦自励是一个人取得成就的根本出发点,而这种精神正是他从小刻苦攻读的延续,也可以视为家庭教育和朋友切磋产生的积极影响。
五、结论
总之,张溥富有成就的人生固然与明末社会政治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抛开其他种种因素不说,张溥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对他的思想形成与人生道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今天的广大家长来说,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就既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个人奋斗结果,还是社会教育的产物。从张溥早年的学习经历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几点:远大的理想始终是学习的强大动力,但这种动力不是建立在空洞的口号之上的,而是要与学习者的生活处境息息相关;教师的专业水平与赏识教育不仅减轻了学生理解上的负担,而且是学生长期保持学习劲头的助推剂,家长对孩子的期许与对孩子学习过程的适度参与,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激励;同学的切磋交流与主动性思考,也是学有所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勤奋刻苦的精神永远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关键因素。
本文作者:陈朝晖 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31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