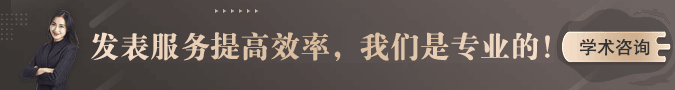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研究
“十七年”文学具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不过,这仍是就总体上而言的,“十七年”文学的特征并不能就此而被揽括。於可训指出:“‘十七年文学’的多种阐释、评价的可能和空间,亦即是它的新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无须到这种高度政治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之外去寻找,它就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这种真实的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是这种真实的历史语境在生成这些文本的过程中同时也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本的间隙和裂缝。”(2)虽然意识形态对”十七年”文学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但在“十七年”文学中,那些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以及在今天看来称得上经典的作品从来都不是极端政治化的作品,而是能反映特定时代生活丰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政治和文学(人)的复杂关系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集体不可分离,它们在特定时代中以“一币两面”而并非以分足鼎立的方式存在。按照政治和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面对文本的过程中我们永远都会疑问:对于“十七年”文学中存在的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发言,还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发言?想给这样的问题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运用这种思维进行研究既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样态,也不能使新的文学史研究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因此近些年这种方式的研究已受到不断的批判和清理。
“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它体现了政治与文学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学必须担负起弘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弘扬”违反了文学的精神,那么,它势必也对政治的宣传无济于事。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必须从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与文学(人)的关系出发,这里之所以不再关注政治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种“历史化”的思维下,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存而不论,而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中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十七年”文学有它特殊的处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个人的方式,其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也是多样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具体地说,在“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中,既有政治化倾向明显的作品,也就是政治性高于文学性的作品,也有政治和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有少数的注重个人文学表达的作品。而在每个作品的内部,其政治和文学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地方的描写比较政治化、理念化,而有些地方又能够把政治与人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还有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富有生活情趣并暗含一定的个人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多层次性即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创作上,也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就拿“十七年”文学对情爱的表现来说,就既有被政治规范的革命化、阶级化的情爱描写,如《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描写就是以强调革命对于情爱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也有对革命、阶级中的情爱的合理表现,如《创业史》中对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描写,就既包含了革命理性对情爱的制约,也包含了情爱的力量和革命理性所构成的冲突和矛盾;还有通过间接、婉转的方式对情爱本能的正面表达,如《山乡巨变》中多次对盛淑君和陈大春在约会时不经意的身体接触的描写就传达了作者对情爱本能的肯定;甚至也有对跨越阶级阵营的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表达,如《辛俊地》中对革命战士辛俊地和地主女儿桂香的情爱悲剧的描写就包含了政治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这些情爱描写方式都是“十七年”文学所特有的,表达的是作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由此,我们不能再单纯以“压抑”和“被压抑”的模式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欲望表达,政治中的个人有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呈现方式,并且,它们可以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一种多维的张力关系。
“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存在多种政治与文学(个人)关系的表达,有些是主流的、显性的、与政治比较合一的文学形态,有些是边缘的、隐性的、与政治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形态,也有一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学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七年”文学文本内部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的杂糅。对此,詹姆逊的解释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他认为,“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4)“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各种叙事形式的共存,可以是一种和谐的张力关系,当然对于具体的文本来说,是否能达到“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如何,这又要具体分析。有人说:“十七年”文学“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5)。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人才会看到不同的文学史风景。而既然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那么,如何在这种“纠结”中对“异质性”的内容进行把握就成了关键。所谓“异质”,当然“异”的是政治的“质”,但对“十七年”文学来说,这种“异质”只能是相对的,关注“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化的、审美化的表达,并非是要以某一种固定的价值为标准。洪子诚表达他对“个人”的理解具有启发性,他说:“个体的价值选择的独断性质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不应推论为普遍性的,进而要求其他人无条件地接受……如果把价值选择完全看成是个体的问题,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质。要是我们也认同下面的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独善其身的‘逍遥’,而且要有‘拯救’的承担,那么,在‘价值多元’的境况下仅仅强调选择的个体性质,这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6)虽然不能说任何对“十七年”文学中“非主流”性质文学的研究,就是剥离于特定时代语境的带有主观性的研究,但对这种文学存在状态的阐释是否符合文本的系统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结构却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由于我们惯用一些理论术语和文学史的线索对20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进行评判,比如一说到“个人”马上就会想到“五四”启蒙传统,虽然这样一种联系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但不能忘记的是,“个人意识”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它也是人性本然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意识中除了政治理性,也会有生命感性,作家也会有对人的感性世界表达的渴望和冲动,这并不都是来自于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十七年”文学是如何体现上述那种多层次性,或者说在文本研究中哪些方面的特点特别值得注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细节”比“主题”重要。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通常是清晰明确的,作品在总体上的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的安排是围绕某一主题而设置的,但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并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在文本的无数细微处往往包含着主题所不能涵盖的内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细节的政治”,“细节被界定为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现呈,与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vision)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些宏大的眼界企图将这些细节纳入其臣属,但却出其不意地为这些细节的反馈所取代”。(7)往往是在对细节的剖析中,我们能看到主题表达以外的内容,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所在。
其次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对于探究“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而言,某些题材的文本具有更强的可解读性。在“十七年”文学中,往往是那些反映革命战士成长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的作品会充满一种“多声部”的特征,即体现不同话语的斗争和纠葛。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确定的,但在对“成长”和“改造”的过程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在“十七年”文学中,即使是那些将个人和政治被认为结合得较好的作品如《三家巷》《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这种“结合得好”很多时候只是在文本的理性表述层面所取得的“胜利”,它带有作家对人物主观干预和塑造的性质,虽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宝、林道静等最后的人生选择仍然是从属于国家和集体,但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流露出的感性、个人的力量,仍然给文本造成了缝隙,这也正是这些作品被反复批判的原因。
再者是“经典文本”比“普通文本”重要。由于“十七年”文学总体上比较统一的特征,当下研究展开的重点仍然在对经典作品的“重读”上,因为经典的作品不仅能涵盖同时代一般作品的思想和写作特征,而且由于其在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上的有力平衡,它在对政治、人性关系的理解上也就能远远超越一般作品,由此,它所提供的文本的复杂程度也会大于一般作品。洪子诚就坦言道:“我也是想能发现50-70年代许多被‘遗漏’的、‘另类’的东西的。我不相信那个时期,人的情感、观念、表达方法就那么统一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8)
当然,以上“两个重要”也都说明“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9),这才是文本研究的关键。当然,以上所说的这种多层次性对于文本来说并非固定的,而是变化的,这是因为很多“十七年”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大都再版、重版过,而在再版和重版中,作者对原作进行删改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只是这种“删改”很多时候是根据现实要求而非文学要求进行的。这样看来,“十七年”文学的不同版本与现实政治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红岩》等作品在不同的版本中所呈现的各种话语的强弱关系、组织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版本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调整,当然删改的方向只会是越来越靠近革命话语和阶级规范,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十七年”文学,我们不能笼统地就小说发言,而必须根据具体的版本来发言。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与现实之间强烈的对应性,它才会有激烈的随着现实变动的不稳定性,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复杂之处。总之,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在文本自身所反映的复杂性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结合的多种可能性所带来的文本的多层次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学史研究中,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科学理性的研究心态和价值立场,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从理论上来说总是第一位的,这也被看作是每一个“治史人”的基本职业素养。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要“永远的历史化”,他认为有两条实现的路线:客体路线和主体路线,即研究对象(文本)的历史化和研究主体的历史化。(10)所谓“历史化”,即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对历史的态度就是关注历史形成的过程和肌理,而不作主观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历史观念的影响下,“十七年”文学研究近些年的发展也显示出“客观化”的还原历史的努力。不过,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纯粹客观的文学史写作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也是很多学者在实践中普遍感到的困惑。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就提倡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考古学”立场,而李杨却指出,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并未很好地贯穿这种立场。洪子诚回应说自己的研究中确实存在主观上的“启蒙主义立场”,并解释说:“我在《文学史》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11)李扬自身虽然在1990代末的研究中力图贯彻一种科学、客观的立场,但他在对“十七年”经典的重读中也并非没有价值判断和立场。逃离价值立场也是一种立场,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是必须的,但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方法的使用都不是绝对的。
“文学史”的特殊性在于它考察的对象既是历史,也是文学,西方新历史主义把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文本,具有虚构性,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也是文本——文学文本,文本的呈现方式是语言化的,我们只能通过语言走近历史,历史在被我们“还原”或“阐释”的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叙述的方式进行,而我们叙述历史背后的方法、立场和语言却是多变的,因此我们所呈现的“历史”会呈现出多层次的状态。对此,我将具体结合“十七年”文学具体的研究状况进行说明。第一,进入我们视野的“十七年”文学文本本身就具有多层次性,对此,通过上述“十七年”文学中政治与文学(人)关系的多层次性的论述已经进行了一定说明,“十七年”文学政治与文学(人)关系的多层次性也必然会带来通过文本重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里的“历史”既包括文本所指向的文学史,也包括文本外现实的历史。有人认为文学史主要是审美的历史,而对社会生活没有责任,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文学是一定时期社会和个人生活直接、间接的审美的反映和表现,它的内容不单包括审美的历史,也应包括现实的历史,也就是说,不仅历史事件在讲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文本也在讲述现实的历史,王德威说:“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12)而由于“十七年”文学与现实之间较强的对应性,我们在面对“十七年”文学的时候,更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学和历史联系起来思考。在考察文本的历史性时,除了普遍适用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之外,当下学界所提倡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性”的发掘显示出特殊之处。这一研究方法的目的是重建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它倾向于透视文学史背后的形成肌理和组织方式,同时对剖析权力结构中话语如何被组织的过程有一定优势,如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的研究思路,关注的就是“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和描述的。在文本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提倡这一思路,“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文本时,最重要的并不是从中寻找和发现某一个因素(如个体生命欲求等)并对其作出价值评判,而是阐释各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组合方式。”(13)
也就是说,与以往文学史注重价值判断不同,“谱系学”性质的文本研究放在了“如何写”而不是“写什么”上,如果说通常的文本细读只是对文本的主题、情节、人物等表面结构的分析,那么“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则重在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它能从另外的角度提供文本的历史性,即文本在叙事上的特点是由何种机制形成的、何种话语操控的,如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专著就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思路。不过,总的来说,在近些年“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文本实践中,福柯在思想观念上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影响要比其在研究方法上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影响大得多,这种“思想观念”主要指的是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由于“十七年”文学存在比较突出的政治话语对文学的组织和限制,福柯的这一理论看似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就具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实际上,把“权力”等同于国家政治是对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的简单化理解。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中的“权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权力”有很大差别,它更多是指由知识、话语的生产所形成的权力网络,同时,福柯对权力话语所作的历史性的分析,说明权力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并非想象的那样是“压抑”和“被压抑”的关系,不过,他的这种学术思想却较少对我们的“权力”研究有启发。与“十七年”文学高度政治化的语境相对应,很多研究者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一些研究结论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即承认权力话语对人的规训,人只是权力的被动服从者,这样的研究思维不能体现作家及文本的感性主动性,势必会对具体的文本缺乏仔细分析和研读,结果造成“十七年”文学研究出现了和过去以阶级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学史研究同样简单化的倾向。同时,从思维特点来看,话语分析方法具有思想史、社会史、历史研究的特点,这对文学研究来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缺陷,因为它偏向于理性和逻辑,缺乏对感性世界的细致感受和把握,用它来研究文学并不能显示出其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话语研究的区别来,也就是说,话语研究更适用于研究普遍性问题的抽象学科,而不太适用于个性突出的文学研究。所以,倡导“谱系学”研究方法的李杨在面对“十七年”文学文本的时候,仍然说:“在目前包括‘文学生产’‘一体化’‘知识-权力关系’等众多新鲜有效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方法之中,我仍然选择十年前确定的‘再解读’方式进入历史。”在面对文本的时候,如果说感性层面需要的是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精神对话,那么,在理性层面,需要的则是研究者对不同的文本所具有的结构关系的把握,这两种文本研究方式都不是用权力话语理论把文本处理成单一的结论。第二,除了以上所说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多层次性以外,文本的历史性也与研究者所处的当下语境、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价值立场等有密切关系。没有主体对历史的介入就没有历史,这包含着历史叙述无法摆脱的悖论:当历史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过去,历史的真实只能通过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获得,当代人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包含着他们自身的精神状况对历史的介入,在这一意义上,文本历史性的多层次性也是由研究主体所赋予的。
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种观念的提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立场的出现都是由当下语境决定的,“复苏五四启蒙传统”“重申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寻找人文理想”“重塑时代精神”等一个又一个的文学话语类型和研究热潮实际上都隐含着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和价值立场,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福柯的那句“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仍具有真理性。因此,如果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描述都多少包含和融入了阐释者所处的当下时代语境的因素,代表着在历史中寻求答案的冲动,那么,历史永远都不会只代表消逝的过去。在福柯那里,对历史的知识谱系学的分析,就是源于现实的冲动:“我起初是从一个用当代术语表述的问题出发,我想弄清它的谱系。谱系意味着我的分析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的。”也就是说,所有“历史性”的研究都会受到当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当代性”赋予了历史多层次的品格。实际上,正是上述一个又一个的“当下语境”给近二十年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打上了各种各样的烙印。同时,由于当下很多“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者都曾亲自经历过那个年代,因此,对文本的历史性研究也会受到研究者个人经验的影响。由于“十七年”特殊的历史环境,每个人对它的个人记忆是不同的,有些人对“十七年”有着深厚的“红色”怀旧情绪,这些主观的感情不会不影响到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判断。有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对此发言道:“我们一方面试图把文学史的写作变成一种冷却抒情的‘叙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取客观与超然的学术态度,同时又发现,当我们自己也变成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由此看来,并不是‘当代人’不能写‘当代文学史’,而是当代人‘如何’写曾经‘亲历过’的文学史。它更为深刻地意味着,我们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16)因此,在主观和客观、情感与理智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在对历史的理解同情和对历史的客观审视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良心和责任感,都无疑是对“治史人”的挑战。再者,对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也受到研究者在一些文学问题上的价值立场的影响,这同样是构成文本历史性的多层次性的重要方面。由于“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创作原则上的特殊性,它的文学创作原则和标准与其他时期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同时,其他历史时期如“五四”所形成的文学观念也会影响到“十七年”文学批评,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其差异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就会一起呈现出来,如对柳青《创业史》中人物的评价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下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它们和上述问题在本质上仍是相同的。例如令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很真实感人的作品,现在看来却是虚假的,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这显然是由不同时代语境中的不同文学观念所致,但这样的解释远远不够,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似乎仍然必须回答:对于文学史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历史语境中的真实,还是某种普遍性的真实?让我们的研究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即意味着承认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但这样也会带来问题,因为没有价值立场就意味着失去批判立场。在我看来,尽管由于上述不同的主体因素的介入会形成对文本不同的价值判断,但这些不同的价值判断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只能具有某种唯一的真理性,而是相对于还原历史的可能来说,它们是可以共存的,因此这里我仍然认为它们构造了文本历史性的多层次性。实际上,“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孙歌在研究日本批评家丸山真男时指出:“面对历史现象,从外部对它进行批判比较容易,但是这种外部的态度很难深入到对象中去,不具备瓦解它的内在逻辑的功能。而‘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深入到对象中去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它的难点在于很容易被对象同化,因为认同式的‘理解’而丧失批判精神。所以丸山说,‘理解他者’,‘理解’并不等于‘赞成’,它不包含把对方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意图。”(17)当代人的主体精神对历史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意味着当代思想文化、社会语境与历史之间展开一种积极对话的关系,从而使这一学科具有回应现实的能力,历史语境因“当下”而变得鲜活而有意味,当下语境也因“历史”而获得反思和批判自我的能力,这样才能形成“历史”和“当下”的互动。
综上所述,无论是“研究客体”还是“研究主体”,它们的“历史化”过程都充满了多种可能,这些不同的因素共存在文本中,面对并承认这种不同层面的文学表达在文本中的共存相对于拿一种对立的眼光去看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更理性的选择,伽达默尔说:“作品呈现在读者心目中的实际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历史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18)他的这一看法与詹姆逊“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区分纳入一个整体”(19)的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些观点启发我们,在面对文本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重历时性形成的各种观念对研究立场的不同影响,也应该注重这些不同的历时性观念在文本中所形成的共时性的结构关系。(本文作者:李蓉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25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