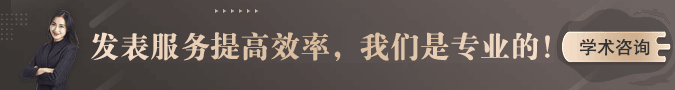小议宗教对当代文学的价值重构
一、族属文化认同中的宗教情怀生成
对于新时期西部小说而言,文学与宗教的关联首先来自于作者的族属身份,而作家之所以将对某种宗教的理解融入文本,就在于边地文化中宗教文化对他们的隐形影响。中国西部边地文化存在着多维性文化结构特征共时结构的多维性组合与历时形态的多维性组合。前者指西部边地文化中,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以及中原儒家文化互相融合,后者指西部边地文化中,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互相交汇。在这种多维性文化机制中,以伊斯兰文化为本色的宗教文化显得尤为突出,“伊斯兰文化精神在中国西部文化的历史构成中始终体现出强烈的精神内聚力和心灵感召力,并成为西部文化鲜明的精神旗帜与优势文化资源。”③对西部宗教文化的关注与表现,由于不同作家与宗教的疏离关系、理解差异、内化方式等不同,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也大相径庭:有的作家从文学创作伊始就显示出浓重的宗教文化特色,如石舒清、李进祥、阿来、扎西达娃等本土型西部作家;有的作家则是在族属意识复苏和族属身份认同之后才显示出刻意回归的倾向,如张承志、查舜等曾寓居外地的作家;也有一部分作家虽非少数民族身份,但其精神世界和思想倾向由于深受宗教文化影响,已经表现出对宗教文化的亲近与逼近,如红柯与伊斯兰文化、雪漠与佛教文化等。但无论是哪类文学出场形式,宗教文化之于作家的主体世界和思想观念的决定关系是其共同之处。由于深受宗教文化的浸润,创作主体会逐渐形成某种心理定势与美学定势,作用于西部作家身上,就是他们普遍怀有“宗教情怀”或“宗教情结”。可以说“宗教情怀”或“宗教情结”是宗教文化投射于少数民族作家深层心理结构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视点,而恰是在这种情怀或情结的观照之下,西部小说尤其是西部民族小说,才显示出其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精神品质与文化特性。
西部作家的宗教情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情怀,是指民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意或无意地将属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意象呈现于文本中,有意或无意地运用某一特定的宗教思维或教义来思考人生、观照命运,以此彰显出文学的民族独特性。这种宗教情怀与作家的特定宗教信仰有关,不同的宗教教派信仰者,在作品中所使用的文学意象、文学语言,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甚至思维方式都有差别,但以宗教文化为底色,力图呈现某一民族和特定宗教的美学气质是其创作旨归;广义的宗教情怀则是一种人文观照精神,是一种深厚、普遍的人生终极关怀意识,“人生的本质问题或核心问题乃在于对生命意义的追究,而这是一个关涉‘实体世界’的终极性问题。这一问题乃是宗教关怀的真正领域。”④宗教所观照的是人类的终极需要,“所谓宗教情怀,就是在这种终极需要激发下所产生的一种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普泛的情怀。”⑤广义的宗教情怀不需要具备物质化和仪式化的宗教符号来营造,但却需要深厚和深邃的信仰与思想来营造和支撑。广义的宗教情怀所关注的,是直面人生的生存困境,重燃人生的生命渴望,追问存在的终极意义,正如周作人1921年在《圣书和中国文学》中所说:“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⑥宗教情怀表现在文本中,就是怀有宗教情怀的作家不管是否是有神论者,是否对某种宗教怀有虔诚和执著的信仰,是否矢志不渝和身体力行地宣谕某种教义,都对人性、人生、生命、精神、信仰等怀有敬畏感、神圣感和崇拜感,对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进行着积极的思考与探索。因此,广义的宗教情怀,因为试图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无法用理性解决的精神问题与存在问题而构成了别一类的生命哲学和生存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宗教情怀与宗教信仰并无必然关联,只要作家具备了超越世俗、回归本质的精神品质,他就具有了宗教情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人是否信仰某种宗教与他是否具有宗教情怀并没有绝对对等的关系。”⑦宗教文化在回、藏两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维系本民族兴起的一个根本点。回、藏两族作家的宗教情结,是回、藏民众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文化浸润下共同铸就的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和文化系统机制,它以隐性力量的方式制约着本民族民众的社会伦理、心理素质、道德价值和审美取向。
二、解构语境中的正面性民族品格弘扬
世纪之交以来,许多作家在世俗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妥协,他们或沉溺于对作品叙事技巧和语言迷宫的卖弄,或以冷漠的心态看待人生的悲苦与人性的丑恶,甚至在一些作家笔下,“审丑”成为一种创作情结,对精神世界与生命意义的追问已经遭到了市场和作家的双重抛弃。而西部作家立足于本族文化,不仅在文学中演绎着西部边地乡土人生的悲欢离合,而且还对宗教文化之于人类精神与当下生活的价值进行着不断的开掘与思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西部民族小说始终将民众身处边地境遇却不失人性的积极正面力量作为主题表现在文本中,通过对本民族优秀品质的弘扬,来传达西部民众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理想的坚守。中国西部地区聚居着大量的穆斯林,他们坚忍、正直、善良、淳朴、安谧、释然,这样的民族性格不仅是他们的人际交往伦理,也是他们对待人生无常与生命坎坷的生命伦理。这些品质看似平凡却饱孕光辉。在东与西的对比,纯与污的对比,善与恶的对比,躁与静的对比当中,宗教文化不仅使回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道德体系产生了深切的认同感,而且凝聚为他们的一种集体性宗教情结,成为他们观照乡土人生、书写人世沧桑的主要视角。他们对本民族优秀品质的弘扬,不仅弥补了汉族文化日益孱弱的精神现实,而且也吸引了身处西部地区但并非回族族籍的作家。比如新疆很多作家虽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却一致肯定伊斯兰教民族精神中的诸多优秀品质。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些优秀品质化为创作的精神指向和文学命题,探讨着这些品质力量所具有的人类性与共通性,从而使伊斯兰宗教文化精神在当下混杂而粗鄙的文学格局中,显示出希望之灯的航标功能。如非伊斯兰教信徒的作家哈丽黛就认为“弃恶扬善”是伊斯兰一个很好的伦理准则;哈萨克作家哈依霞•塔巴热克则充分肯定了伊斯兰教的“正面、规范、震慑力”等价值。这些非回族籍的新疆作家在深刻认同伊斯兰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在作品中也塑造了许多体现回族优秀品质的道德模范形象,以此来弘扬和彰显一种宗教化的道德风尚:“宗教者所以维持道德也,维持道德乃宗教之本质也。”⑧汉族作家红柯早在大学时期就对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通读《古兰经》,而且还将西部和新疆作为他一系列小说的空间背景。西部民族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将其诸多优秀品质和宗教理念化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且还表现为他对伊斯兰民族优秀品质的展示和弘扬中。小说《东干人》主要叙述作为回族分支的东干人在清政府的围剿下所经历的民族苦难与生存磨砺,最后,他们只能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对伊斯兰民族历史的悲悯与深情展望,对其信仰的虔诚、执著表现出了深深的钦佩与崇敬;另一方面作者则是力图通过对东干人在民族磨砺境遇下所表现出的坚韧、隐忍、不屈等民族品格的高扬,来表达一种对刚性和血性精神的呼唤,而这种刚性和血性也正是现代文明异化下的东部都市人所最为缺失的。《帐篷》则集中展示了红柯对伊斯兰民族宽容品质的青睐。海布将怀有身孕的苏拉抛弃,但苏拉却没有充满埋怨、企望复仇,而是从大自然最简单的自然演变规律中,认为自己长得越来越丑是被抛弃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宽容成为平息内心愤怒和化解人际冲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宽容也成为伊斯兰民族得以隐忍并默默生存下来的集体性格特点。诸多的民族性格,我们可以在石舒清、李进祥、马玉梅等众多回族作家笔下找到,伊斯兰文化影响下回族民众的优秀品质,不仅与当下人性异化的现实存在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也传递出民族作家试图重建完美人性、重振传统伦理的文化诉求。
三、世俗语境中的超越性精神信仰重建
一个人怎样才算是真正皈依宗教?检验皈依宗教的精神标准是古今中外宗教精神的一个古老命题。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个人必须加入某个宗教组织,遵守某种宗教制度,才是真正皈依。也就是说无论心灵是否真正理解宗教、认同宗教,只要一入道门、佛门等,就可以瞬间脱离世俗纷扰与凡人拥嚷,获得精神的超脱、实现灵魂的净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否从制度上和礼仪上来皈依宗教,一方面应该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对宗教制度的认可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对宗教精神的认可,而之所以加入某种宗教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外在制度、内在自守以及身份认同和身份彰显方面达到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宗教礼仪和宗教精神之间还存在错位的现象,即不参加某种宗教礼仪并不代表没有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认同某种宗教制度也并不代表真正领悟了宗教精神。因此,中国的宗教观存在着制度认同与精神认同的错位现象。西方国家由于宗教思维的非功利性和理性思维的历史传统,他们对宗教更侧重于自我反省和精神追问,他们往往试图用理性和感性的哲学观和生命观去看待生老病死、人世无常等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总是试图在理性、哲学的探索中构建某种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正如蒂利希对宗教的看法:“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⑨伊利亚德也曾说“宗教”应该作为一种“人类学常数”,⑩“宗教思想,不一定有任何组织,任何制度,在原始人类以至于现代文明人中,日常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崇拜与神秘思想,都是属于它的范围之内。虽不必人人都有宗教的信仰,却不能说人人都没有宗教思想”,“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因此,从广泛意义上来看,宗教精神的本质,不仅只是宗教仪式的完成、对未知世界的盲目崇拜、对人生困惑的精神诉求,而更应该是对某种精神和信仰的虔诚坚守,是坚持不懈的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以及对人性、生命、灵魂等人类共同的存在命题和精神理念的虔诚敬畏与神圣体验。
在当下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相交融的价值混乱的文化背景下,宗教精神或精神信仰的重建显得尤为重要。纵观20世纪思想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精英在借助西方启蒙、科学、理性等现代观念扫除封建主义的愚昧而将“理性”推崇为人的自由存在的本质之后,随着科学、技术与理性的过度膨胀将现代人对生存的体验打入黑暗深渊时,我们又借助消解、颠覆、反传统等后现代理念将启蒙、理性、上帝等这些曾让国人敬畏的心灵之神推翻。权威的树立带来精神的荒芜,而权威的瓦解同样会带来精神的空虚。在经历了树立与瓦解、建构与颠覆的交迭历程之后,结局却是价值的混乱、精神的困境,以及信仰的放逐。因此,重建精神家园、拯救灵魂危机,就成为当代中国多元文化境遇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西部民族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情怀或宗教精神,在这样的社会集体性心理诉求之下,显然就具有了拯救与重建人类精神症候的现实意义,“作家有意识地唤醒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就会以一种敬畏、神圣的心情和肃穆、虔诚的态度去重新思考社会、人生中的精神价值问题,去追问自然和生命的本质,去谛听未来文明传来的振幅。”新时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怀有深厚伊斯兰宗教情结的回族作家就将信仰大旗和宗教精神作为自己介入当代文坛乃至当代文化的一种独特姿态。西部作家用宗教精神来面对世俗的困扰、生存的逼仄、命运的无常、人生的厄运等问题,无论是用隐忍来沉默地承受苦难,还是用决绝的姿态反抗对信仰的亵渎,抑或用“清洁”的精神随时反省自己的灵魂、洗涤污浊的世俗尘埃,他们都始终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虔诚与道德的自律。而这种自觉意识的形成不仅是个体,更是集体性的坚守姿态。虽然他们用“真主”之神来作为约束现实和精神的隐形力量,但这种自我规约与自守坚韧则是伊斯兰民族集体性格的历史传承,在当代价值荒芜的境遇下显得尤其难得可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回族作家是用本民族博大而深厚的宗教资源和文化资源赈济着时代精神,“宗教使人认识到人类虽然有卓绝的巨大能力,但也仍然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得和自然共存。对于一个具有意识的存在因而就有选择力,就不得不面临某种选择的存在来说,宗教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东西。人类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
无论是张承志的清洁精神,还是石舒清的诗意安守,抑或是李进祥的人性自省,贯穿始终的是对信仰的坚守,他们不仅成为作品主人公用来应对生存困境的文化抉择,同时也是作家自身对现实处境所做出的一种生命选择。如《心灵史》不仅探讨信仰什么,还探讨了怎样信仰的问题,“不畏牺牲、坚守信仰”就是作者所要昭示的一种信仰姿态,由此类推,张承志将信仰问题深入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高度,探究着人类共同的精神问题:“他没有将目光只停留在狭隘的民族情感上,而是透过回族人的生活与命运,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上去表现更深层意义上的人生,将民族性与历史性很好地统一起来,包括了更多的社会意蕴”,他的“文学始终激发人们寻求理想生命意义的价值,执著地追寻着道德意义,这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强壮的生命体魄,并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宗教子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以死捍卫信仰的“男子汉”力量的决绝与强劲,不仅是当下萎靡颓废的时代精神的一针“清醒剂”,也从正面传达出了在价值无名时代,人应该保有对理想、幸福、信仰、希望坚守的执著与勇气,应该保有对人类生命问题和精神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这正是宗教文化进入文本之后,为民族精神重建和精神理想重建所提供的一个独特思路。
四、狂欢语境中的悲剧性美学风格开拓
宗教情结制约下的文学宗教性书写,引领着世纪之交文学悲剧性美学风格的开拓。中国文学向来只有悲情而缺乏悲剧,而“悲剧意识来自民族意识的回归与强化,来自对民族历史命运的反思”。因此,张承志、查舜等民族题材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从民族历史的钩沉中,挖掘民族先祖的苦难历程,而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因为有着对信仰的执著而遭受到了生命的洗礼、放逐、侮辱、屠杀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因为有着精神的信仰而显得悲壮而崇高。回回民族自唐代开始就为了在本土扎根生存而奔波抗争,无论是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和波斯人为了弘扬伊斯兰的宗教精神,还是迁移到中国的穆斯林为了信仰而不屈地反抗清政府的血腥屠杀,其民族的成长总是与苦难、压迫、牺牲等相伴,“尤其是‘族在旅途’的特有度世方式,起源自阿拉伯祖先驼背文化的深远影响,‘断了归所’的漫漫长旅,令回民不得不感到‘路上更具故乡遥远’,但‘终日只渴望走’,因为自己‘最想的还是流浪’。虽然这颗‘不安的旅人之魂’是祖先造就的。一代代回民的‘ontheroad’,便在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以‘路’为本色的‘路文化’,这和以‘家’为底色的中国传统‘家文化’形成了比照与互补。”经历了苦难的重负、历史的坎坷、现实的压迫、生死的考验以及血腥的炼狱等,回回民族的反抗、隐忍与安守中,更有着无可抗拒的命运不公与生存无奈。“美学悲剧性是指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体自身的精神风貌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展承出人生的全部价值。”以此观照回族小说可以发现,其显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美学悲剧意味。在坚守信仰与屈服压迫的处境中,坚守信仰意味着忍受不可更改的生死洗礼,而屈服压迫意味着失去生命的灵魂,而在这左右突围和抗争中,他们将死亡作为了折中的方式,为了拯救世俗之浊却惨遭屠杀,在坚守中实现了生命的升华与世俗的超越,由此也孕育了回族小说的悲剧性美学追求和文化基调。张承志的《残月》、《终旅》中,哲合忍耶教的先人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延续,为了在权势迫害与世俗侵袭的压力下求得生存,不惜让鲜血染红西部大地,即使如此,仍不放弃对信仰的虔诚;《黄泥小屋》中,主人公苏尕三同样在面对官家的羞辱与折磨中,坚守着灵魂的清洁与人格的操守,在死亡和信仰的抉择中实现了宗教精神的升华。此外《金牧场》中面对死亡的回族老人,《心灵史》中面对屠刀的马化龙,在生存困境的两难抉择中,他们都选择了精神的清洁与信仰的坚守,从而使得这些人物呈现出了英雄主义的悲情与生存处境的悲剧,小说也由此完成了对回民族历史苦难生存经历的艺术化展示。查舜在《月照梨花湾》中对回民族在极端境遇下的生命本质进行了富有探索性的思考和表现。这里的悲剧性不再是血腥屠杀与政治压迫下惨烈的民族生存,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浸润着一个民族不可预知的生命隐秘与生存艰辛,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外在文化权力的挤压,而且面临着对自身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犹疑。而在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消逝的抉择困境中,心灵“乌托邦”的梦想被击碎,唯有本民族充满悲剧性的艰难命运体验留存于民族性的集体记忆深处。
五、结语
世纪之交以来的西部小说,由于渗透着本土性的宗教文化,不仅表现出了在社会普遍性的道德混乱与信仰缺失境况下的精神清洁,而且还通过参照的形式为文学精神的提升提供了一种典范性。尽管西部作家的这种文化姿态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他们宣扬的正面力量、对道德原则的坚守、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姿态,无疑给当下文学精神的荒凉带来了绿色的生机,也给漫游于精神与现实中的流浪者提供着精神的导航。尤其从形而上层面讲,宗教情怀也是当下人面对生存苦难和精神苦难所应该具有的人生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也不乏保守与宿命的色彩,但在现实层面和心灵内里却饱蕴着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而宗教性的小说也因此实现了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对文学品格重建的启示,对世风习俗矫正的警策。(本文作者:金春平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24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