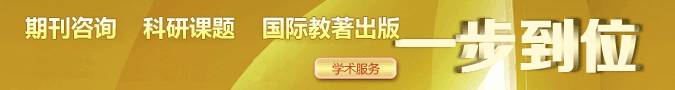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特点
内部发行并非始于文革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著作。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发行的特殊模式,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气候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毒瘤”的危害,一些用于学术和情报研究、反应西方意识形态特征的作品只能限于一定范围内传阅。至文革时期,内部发行方式走向政治极端。一方面中国开始试探性地与西方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身的革命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引进西方著作并通过内部发行的方式以供内部高级人员参阅便自然成为必要的选择。这些内部出版物以行政级别作为阅读资格的标准,认为这些群体具有可靠的政治免疫力,能够把含有“思想毒素”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从而进行自我教育。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译作只有一个目的———供批判使用,其批判的不只是著作的语言或表达形式,更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等内容。如《海鸥》是1974年通过内部渠道译介的一部美国当代小说,其反映出来的不安现状、不断进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了当时内部人员进行批判及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教育的工具。
据统计,文革时期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总数为“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有24部,日本文学作品9种13部,当代美国文学作品5种6部,德国、玻利维亚各一部,另外还有一本翻译文学刊物”[2],这个数量在今天看来确实微乎其微,但在文革这个暗无天日的年代,这些供参考批判用的内部刊物却构成了当时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存在,却为日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保存和积累了一大批有用的文学资料。
导读性文字:对读者的控制
有学者将翻译标准定为“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3]90,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尤其是在历史转型时期,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使译文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而在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文革时期,译者选择译本或翻译策略的主体性虽然被抹杀,但译文读者仍不能与原文读者产生同样的感受,甚至有时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内部发行的译作上(资本主义国家作品更是如此)。这主要归功于该时期的文学翻译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另一独特现象,即内部发行的翻译作品都会附上一篇导读性文章,来限制读者对译作的理解和感受。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说过:“每个社会都会排斥某些思想和感情,……这一社会禁忌对翻译活动会产生较大影响,如某些文本或其特定内容的翻译被禁止,……某些特定的理解被禁止;……那些与特定阶级和社会要求不相符合的内容,即使意识到,也会主动‘克服’掉。”[4]255下面看《海鸥》原文、译文如何在美、中两国读者中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
美国飞行员、作家理查德•巴赫的短片小说《海鸥》描述的是一只与众不同的海鸥,在海鸥乔纳森的眼中,飞行是生命的全部,他追求的是速度、完美的飞行技巧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达到和思想同样快的速度。自1970年出版后,《海鸥》受到了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在他们看来,这只不断学习、奋勇向上的海鸥正是美国70年代的精神写照,因为“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其实用主义文化培养了美国人务实精神、竞争意识。他们乐于开拓进取、自力更生、敢于冒险、重视创新,抱有一种‘凡是都有可能’的态度。”[5]2因此,《海鸥》38周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这足以说明《海鸥》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及其对美国人民的影响之大。
4年后,《海鸥》通过内部渠道被译介到中国,在译文前附有一篇任文钦写的政治性导读文章《海鸥为什么走了红运?》,文章将《海鸥》描述为“一部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涂抹而成的小说”[6]。海鸥乔纳森追求的“自由”、“没有局限”和“尽善尽美”的飞行技巧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有力工具,“自由”、“没有局限”是指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自由地、没有局限地去奴役、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而如果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听从乔纳森的召唤,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就能为资产阶级创造更多的财富。通过这样言辞激烈的政治性导读来控制读者对译作的接受角度,使得海鸥乔纳森在中国读者的眼中成为了狂妄贪婪的资本家化身,自然变成了人民批判的对象。同一部作品由于政治气候、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使两国读者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
政治工具:文学翻译的唯一目的
历史上不乏借翻译以警世之例,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更是带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目的。可以说任何作品的译介都有它的目的和价值,然而在文革这个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翻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它不仅要充当执政党党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工具,还要充当国际上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工具。
从国内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家领导人为捍卫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而发动起来的,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别有用心的吹捧,国内政治气候走向“左”的极端。此时,宣传和文艺部门的控制权掌握在极“左”分子手中,他们充当着翻译赞助人的角色,对译作的选材、翻译的出版等严格地实施操控。一方面赞助人控制下的翻译界把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毛泽东及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上,以突出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取得其信任及亲睐。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私下进行译书活动的翻译家进行迫害,给他们扣上“崇洋媚外”、“反动权威”的帽子,将其批判为“走资派”,从而排除异己。总的来说,这段时间的文学翻译就是为当时掌握着意识形态大权的“四人帮”扫清政治道路的工具,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小集团的帮派利益服务。
就国际形势而言,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在文革时期占主导地位,即一切宣扬工人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好的,相反,只要是受资本主义国家亲睐的东西统统都是应该被唾弃的。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主要为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此外,还有几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他们都被认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得以出版。这些国家在文革期间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公开翻译出版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是带有明显国际外交性质的政治行为。内部发行的文学翻译作品则更能体现出翻译作为特殊时期的政治工具的作用,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资本主义国家著作的译介,其目的仅仅是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人员批判使用,使其成为国际阶级斗争的有利工具。
可见,文革时期的翻译在显性权利话语的影响下呈现出单一的特性,无论是在译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确实都不值得为之吹捧,但特殊的历史环境却赋予了该时期翻译以特殊的研究价值,很多文革时期翻译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只是作为斗争的工具被引入,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文学价值重新为人民所认知。如,今日便有不少人赞美海鸥乔纳森那不屈不挠的开创精神。由此可见,文革时期的翻译研究仍是一块未曾完全开发的沃土,有待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大的精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作者:肖美凤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17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