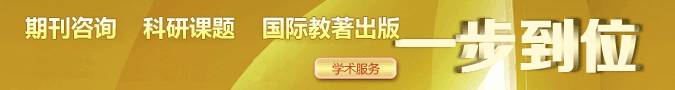西方文学生态文学批评的构建
究其本质,“生态整体主义”仍旧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外沿扩张后的结果。因此,生态整体主义要为文学批评提供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理论,其自身面临着诸多问题。它否认了人类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应有的积极位置,而将自然赋予某种意志,使之来约束和规范人类活动。将这种价值观或理念引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去,无疑是本末倒置。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和生态对于人类来说,都只是人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生态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并不能出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去。将这种思想牵强附会地引入到文学评判中来,不仅拒斥了人的中心地位,而又想强行介入“人学”的一切文本的理论,必然导致文学批评陷入一种进退维艰的尴尬境地。生态批评与其他的文学批评类型(如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相比,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等只标明了范围和方法,生态批评则更清晰地提出一种主张。在文学被视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带来了一定的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基于此,为了让生态文学批评不再是单纯生态意识的传声筒,生态文学批评不仅要具备生态文学外观,而且还要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涉及生态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涵,即观念的传达方式,并形成自己的审美批评原则,这样就面临如何抽取、形成生态思想的审美内涵的问题。因此,构建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是文学文本与生态批评的契合,从而使得所构建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获得范式意义,这就要求其理论思想内涵必须区别于现有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模式、方法和知识系统特征。同时,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认同传统的审美原则和标准,否则,其理论必将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
生态审美原则作为生态批评用以进行审美判断和评价的尺度,应当是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生态审美的生态哲学基础的主要层面包括:生态智慧的构建张力,拓展了生态审美观的哲学视野及思维品质;生态世界观作为践行原则,促成生态审美的现实的美学实践和艺术实践;生态伦理作为运行轨迹,通过生态审美化的生命体验,促发人们深度感受生命的机能及生命活动的意义;生态价值的意义指向,推进并致力于实现生态审美那种充蕴、活化生命价值的能力。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真正的生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原则不能单纯的停留在文学文本所描述出来的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上,而应该将生态的审美本质深嵌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中去,与此同时,生态文学批评过程中的生态审美研究还应该廊括人类社会生存的生态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并且,我们还应该从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找到与生态审美原则的契合点,以此来避免为迎合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性认知而强行制造一种审美意识,从而为人们所诟病。如果这样,则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就是构成对审美活动的根本背弃,注定不会为人们所接受而遭到唾弃。因此,生态批评理论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原则是有诸多不妥的,它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远远不能生存一种生态批评,它不能肩负起给生态观念以及生态批评提供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革命的重担。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态批评理论,注定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构想;生态批评必须吸纳并整合其他理论资源进行自我建构。
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
“生态批评”的生成和兴盛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性渊源和发展性过程,同时它也有着其多样性以及本质性的含义界定和研究模式②。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科学知识的单向度增长并不代表文化进步本身,而只不过是人类的“天真”从“幼稚”走向“深刻”而已,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人—自然”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消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克服科学知识异化的最好办法便是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知识的航船之舵,从而使科技非理性主义理性化,科学知识人性化、科学进步伦理化和科学知识的潜在威胁虚无化。只有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人类才能从消极自我否定转变为积极的自我肯定,科学知识和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伦理学史上的“不对称”与“后果论”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扬弃。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学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③。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仍然坚持认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批评,生态文学批评要完成这一转变,其前提条件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生态危机引发的生态反思与文学文本批评的兼容性问题,必然涉及生态思想如何介入文学批评的问题。从过去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甚至于在某个时候将所有文本都纳入其研究范畴。从最经典的文学文本向民间文学扩展,直至覆盖所有文学文本,以此来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从而建构起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使得这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值得肯定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是从规律文学文本到特殊文学文本,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从书斋到田野,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在此层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也为其完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以着力的附着点。生态批评所运用的生态理论,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生态事实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以文本为目的的批评,生态批评认为文本的生成是“个体”与“群体”创作意识形态阐释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蕴的体现④。文本中的“自然”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说概念发生了游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生态批评自身理论的窘迫:它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下的各种理论的拼接,试图从生态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进行批评,从而唤起人类对环境危机的重视。然而,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它又是一种“他治”的理论,生态批评仅是目的论的艺术观的复活。因此,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所带来的问题造成了生态文学批评在学理层面全面倒退的批评模式———文学批评找了比反思、批评文学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生态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与文学文本批评理论的相互不兼容,仍然是困扰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障碍。
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
生态批评是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对人类活动进行的全面思考,生态文学批评是在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探讨文学文本中关于自然与文学文本关系的文学批评。它所要揭示的是文学文本中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同时在生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及艺术表现形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也不限于直接描写生态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是利用其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生态审美标准重新审视所有文学文本,特别是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其目的是为丰富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意义,分析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局限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从而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美学,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进而它的审美标准也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与批评对象也因此而扩大到由自然、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整个世界,其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美学发展提供了契机⑤。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研究方法,其理论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亟需实现新的突破。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它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的统一展开,构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它走向审美生态场,洞开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新境。从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前面的论述可知,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由最开始的经典文学文本逐步扩展到任何文学文本,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得生态文学批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环境取向”是导致这一趋势发生的内在逻辑。“环境取向”使得生态文学批评下的文学文本具有了环境伦理倾向,它要求研究者和文学文本创作者承认环境的自身利益和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环境作为文学文本的背景,不仅引导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且还塑造人的情感和行为。“环境取向”文学文本视环境为进程,重视神态环境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给生态文学批评带来了重大影响:“环境取向”促进了生态伦理观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建构;“环境取向”影响下的价值观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影响,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的危机不断深入人心,从而使当下的环境生态危机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者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文学文本内部获得文学性;“环境取向”将单纯的环境描述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相结合,展现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及人类活动的相关性。“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不断地将所有文学文本都纳入到生态文学批评中来,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扩充表明生态批评不断吸纳新的理论资源以扩充自身阐释能力的企图。但是,生态批评批评的对象一旦越过文学文本的界限,生态批评即不再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观念的宣言书,这将把生态批评带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鉴于此,从理论构建角度来看,生态批评的理论根基还相当薄弱,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比较片面。生态文学批评试图超越当下其他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的关注,转而向“人与自然”进发,将生态审美意识的建构为手段来改变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但是,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文学批评不会为了迎合生态批评而撬动自己根深蒂固的文本中心,传统审美原则也不会因为生态观的介入而发生颠覆,因此,从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批评的困境陷入绝境。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建构
生态批评面临诸多困境,其本质并非源于文学的自身要求,而是源于全球环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紧迫性,生态批评为了迎合文学文本所属的生态性,未经严格论证仓促“上马”的批评形态。随着生态问题以生态危机形式凸显,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内容之一。在生态批评领域引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积极、和谐的建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一种良性关系,而不是被动、消极的索取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还是在生态环境反作用于人类,人的主体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类永远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通过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可以有效的改善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万物的关系应该是整体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不是破坏性和控制性的,而且是一种通往理想的渠道,是一种认知、体验、面对、促进与演进。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化批评⑥。它的产生既根植于当前生态危机日趋严重这一现实基础,也充分吸收了生态学、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学科及文艺批评流派的一些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家期望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发掘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寻找一种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对立的有机论自然观。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立足于全人类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去探索和总结人类生态行为的差异,及其生态后果的差异,揭示生态灾变的成因及形成机制,以便从中找到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确保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对策。如果能够在生态批评中引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可使文学批评借用社会批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形态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的关系,将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审美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生态批评强调在“文学与生态”问题域中呈现出一种体现人本主义立场和社会批判视角的文学批评方法,即: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来观察和思考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同时,以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本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展开对文学活动中有关生态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全球遭遇生态危机之时,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确立当代生态价值观时,理性智慧比诗性智慧更加重要;中心论的话语模式是一种语言陷阱。“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中包含了当代生态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中重视人的主体活动性,并承认人类的主体性活动对生态危机有能动作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困境,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指导的解决之道,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框架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文学批评,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态自然观。这个观点与“生态整体主义”框架下的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让生态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人学立场的回归,更加重视人类利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思想与文学批评的兼容性困境的问题,文学批评者应该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对传统文学文本中有关生态环境的描述进行研究,同时,从新匡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到文学文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切不能把文学文本中相关的生态问题看做是创作者的偶然为之,而应将生态问题置入整个文学文本的背景中来考量,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优势,寻找生态问题的现实根据和社会制度及文化根源。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研究者应汲取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生产和消费方式来认识生态问题的理论资源,扩大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范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以及“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方法的引入,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从而使文学作品在人学品格上阐释文本的生态意义成为可能。(本文作者:谭东峰、唐国跃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06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