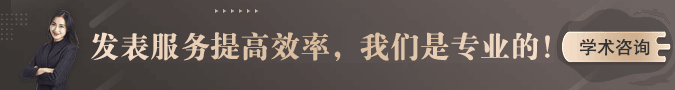保险诈骗共犯的情形探讨
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共同实施保险诈骗之情形
一般情况下,由于保险诈骗涉及多方主体,单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一方难以顺利完成,实践中往往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从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形态。这是保险诈骗罪最为典型的共犯形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主观上有共同的诈骗故意,符合保险诈骗罪共犯的基本成立条件,在具体认定时并无太大的分歧。①不过,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以自伤、自杀或自毁财物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案件中,仍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在自毁财物的案件中,因财产保险中并无“受益人”,所以这种情形的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只能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勾结时成立。只要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事前通谋,故意毁坏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则双方即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在此情形下,投保人、被保险人中的一方即使未实施毁财骗保的客观行为,亦不能阻却共犯的成立。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中一方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毁坏保险标的,另一方只是消极知情,既未与对方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也无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而只能追究毁财骗保者的罪责。但是,如果另一方知情后,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则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如果另一方不知情,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因其欠缺主观故意,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只需依据《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在人身保险案件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共谋以自伤、自杀的方式共同骗保,在此情形下,保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不以参与实施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为必要。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事前无通谋,投保人或受益人在被保险人自杀、自伤时并不知其实为骗保而为之,但在事后知道真相,并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由于在此情形下只能通过“编造虚假的原因”取得保险金,正属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因而可与被保险人一起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②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是在得到保险金后才知晓被保险人的上述行为的,则其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同样只需依《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即可。如果被保险人是在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教唆、帮助之下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则属于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的情形,应根据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以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予以并罚。对此,有论者认为应区分为两种情况分别处理:一是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并罚处理;二是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有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则不需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而只需按“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的方式,以保险诈骗罪的罪名定罪即可,不必再定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③这一观点根据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投保人、受益人给予了不同的处理,它不仅忽略了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构成之可能,混淆了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也有悖于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案件定性的基本立场。通常认为,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对于教唆无责任能力人自杀的,由于被教唆者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对教唆者应以故意杀人罪的间接实行犯对待,依法追究其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④可见,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实施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杀人罪的定性不应产生影响;投保人、受益人在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同时,还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根据刑法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并罚。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无身份者相互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由投保人、保险人或受益人构成。⑤那么,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身份者可以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理论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此处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共同正犯?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刑法理论中素有争议的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对此,域内外也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就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言,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是明确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刑法第31条第1款即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韩国刑法典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但将共同正犯排除在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虽然该规定未涉及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但理论中通常认为,该规定排斥了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可能。①三是对无身份者可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予以回避。例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至于此处的共犯究竟是包括共同正犯的广义共犯,还是仅限于教唆犯、帮助犯的狭义共犯,立法上却未明确,而是将问题留诸学界研讨。与上述立法模式相应,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主张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是日本的通说。不过,学者们所持论据则又有所不同:有的基于共同意思主体说,如日本学者齐藤金作;有的立足于正犯与共犯之区分标准说,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教授等;也有学者将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定位为关于共同正犯之特别规定,如日本学者内田文昭。否定说则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其中,有学者从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角度予以否认,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小野清一郎、吉川经夫以及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等;也有学者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角度加以否定,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山口厚等。折中说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实行行为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如我国学者马克昌教授。笔者以为,折中说更具合理性。因为对于伪证罪、脱逃罪、徇私枉法罪等亲手犯而言,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同时,对于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因其只能由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所以无身份者亦无法成为共同正犯。事实上,由于犯罪构成诸要件紧密关联,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实施刑法中特殊主体构成之罪的实行行为,该实行行为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当然也就无法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②就此而论,肯定说显然是有缺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说全然能够接受。因为正如马克昌教授所言,“在实际上,某些真正身份犯,无身份者并非不可能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否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的可能性,似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不合”③。例如,对于强奸罪这样以复合行为为实行行为的纯正身份犯而言,妇女虽不能实施其客观方面的奸淫行为,但却可以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从而分担强奸罪的实行行为,并据此成为强奸罪的共同正犯。④所以,折中说的立场更契合实际,能够弥补肯定说、否定说所存在的缺漏。具体到保险诈骗罪来说,无身份者能否成为共同正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其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有论者立足于保险诈骗罪是非亲手犯,而认为无身份者可与投保方人员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同实行犯。⑤言下之意,只要不是亲手犯,无身份者即可与有身份者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实际是基于上述肯定说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为笔者所不取。笔者认为,除非无身份者能够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否则,均不能与有身份者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据此,只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作为无身份者能否成立共同正犯的依据。而对于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理论中存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有论者明确予以肯定,认为从立法的规定来看,保险诈骗罪是一种复行为犯,并且是一种紧密型复行为犯。⑥不过,张明楷教授却认为,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而此前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不过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①这实际上是将保险诈骗罪视为单一行为。结合刑法第198条的罪状表述以及诈骗型犯罪的行为构造,笔者认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复合行为。因为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目的的实现,而只有结合了行为人的行骗行为,即接触到具体的行骗对象并传递虚假的信息的行为,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也才能使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得逞。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是最终骗取保险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行为,其本身具有内涵的独立性和欺诈性;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则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具体外化,是保险诈骗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两者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缺一不可。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保险诈骗罪是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的纯正身份犯,但因为其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无身份者亦可参与实施其中的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所以也可以与有身份者一起构成共同正犯。当然,如果无身份者未与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勾结,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径直冒名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应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构成保险诈骗共犯之情形
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争议多集中于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该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特别规定;二是该款是否为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
(一)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界定
对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刑法理论中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二是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②据此,刑法第198条第4款并没有改变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即鉴定人等只有在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诈骗保险金之共谋的前提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时,才构成保险诈骗的共犯。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属于对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在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只具有单方面故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因为其故意是单方面的,而非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④笔者认为,刑法第198条第4款属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而非一般注意性规定。主要理由在于:首先,刑法第198条第4款在用语上与以往刑事立法中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大相径庭。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存在诸多关于共犯的注意规定。如,刑法典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这些规定要么侧重“通谋”,要么强调“勾结”,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共犯的构成予以明确规定,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成立条件;即便没有这些注意规定,按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⑤可见,立法上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需要通过“通谋”、“勾结”等规定来明示共同犯罪故意。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却并未强调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合意,明显有别于其他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由此出发,该款似应涵盖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但因主观上与他人未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后一情形即是刑法理论中所谓的片面共犯。①通常认为,片面共犯的情形虽属客观存在,但并非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②刑法第198条第4款将片面共犯也纳入共犯论处,显然是对原有共犯基本规定的突破,只能属于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简言之,将该款视为共犯的特别规定,正是立足于不认可片面共犯的通说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普遍承认片面共犯,该款就不是什么“特别”规定,反倒应是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了。③其次,不能基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与第229条之间的竞合关系而认定其为注意规定。有论者认为,鉴于该款与刑法第229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第198条第4款旨在提示司法人员,对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条件的行为,不得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④笔者认为,此一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该款是针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而规定,其中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虽为中介组织人员,但证明人却不一定是中介组织人员。在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情况下,有时并不存在与第229条竞合的问题。即便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如果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相信以现今司法人员的素质,也不至忽略保险诈骗罪共犯之构成,而偏执地适用第229条的规定,因而此处似无提示注意的必要。作此语焉不详的所谓注意规定,反倒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定性上的混淆,甚至可能将并非中介组织人员的证明人也不当地纳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范畴。再次,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定位为特别规定,既不会妨碍对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的处罚,也不排斥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对于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有学者认为,倘若将该款视作特别规定,那么,其他行为即使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成立条件的,也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且,在类似的条文中,如关于金融诈骗的其他条文,没有设立与本款类似规定的,即使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亦不得以共犯论处。⑤这一见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该款只是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而并未排他性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只限于上述情形。因此,该款并不排斥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构成之可能,一般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自可根据共犯的基本理论来认定处理。另一方面,在其他类似的条文中,虽未设立与该款类似的规定,但如果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当然可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相反,若行为人主观上与他人欠缺共同犯罪的故意,虽有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行为,亦不能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因为该条文中并没有类似于第198条第4款的特别规定。最后,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视为对特殊主体的特别规制,能够彰显其独特的立法价值,更为契合立法原意。在保险行业中,保险公估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业务便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保险理赔提供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有必要对保险公估业加强法律规制,并对其设置更多的法律义务。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即是对保险公估业中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特别规制,适应了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事实上,将该款视为特别规定,也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的解释,鉴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所提供的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方面的材料,直接影响保险事故调查结果的真伪,因此,“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如果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条件,则以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⑥。这一解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立法者的意图,即上述人员由于主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保险诈骗犯罪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对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行为应当严厉惩处,①而无须拘泥于他们与保险诈骗者之间是否形成共同故意。
(二)刑法第198条第4款之理解与适用
在认可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为保险诈骗罪共犯特别规定的前提下,究竟该款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还是既包括片面共犯也包括普通共犯的规定,学者们亦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该款属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从文义上分析,其不要求共同的犯意联络,也与刑法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用语不符,是由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对于特殊主体予以特别规制之应然价值。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款既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虽未与保险诈骗者形成通谋,但明知投保方人员旨在骗取保险金,仍然为其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诈骗提供条件的,而此时保险诈骗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也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与实施保险诈骗者通谋,为保险诈骗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况。③前者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而后者则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普通共犯。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为合理可取。因为第198条第4款只是规定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并不以其与保险诈骗人之间具有“通谋”为必要。前一观点将该款仅局限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是不适当地排除了双方“通谋”的情形,有违立法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该款的立法宗旨在于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特殊主体给予特别的规制,以适应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形势,至于这些特殊主体与保险诈骗人在主观上是否有犯意联络,则在所不问。据此,笔者认为,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的共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只能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此处所谓“证明文件”,既包括有关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原因、损失程度等情况的证明文件,也包括有关的鉴定书、财产评估报告等。第三,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可以具有为他人骗取保险金提供条件的单向故意,也可以出于与他人骗取保险金的共同故意。第四,行为人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在客观上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了条件。如果行为人虽然为他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但虚假证明文件并未被用于保险诈骗,则行为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特别共犯,仅可能构成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④
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第183条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据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就涉及对此等保险诈骗的共同犯罪究竟是定性为保险诈骗罪,还是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上历来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上述人员相互勾结诈骗保险金的,是定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还是保险诈骗罪,应根据双方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确定,即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性。⑤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罪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与诈骗犯罪人相互勾结共同诈骗保险金的,是保险诈骗的共犯,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处罚。⑥第三种观点主张,投保方和保方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情况,实属投保人等利用保方人员进行犯罪,应视具体情况依照保方人员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之便构成的犯罪对各共同犯罪人以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论处。⑦第四种观点认为,投保方与保方人员共同故意实施诈骗保险金的行为,若保方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共犯;若其利用职务之便,则根据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分别构成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①第五种观点认为,应以实行犯实行行为的性质为基本标准,结合刑法的相关特别条款,考虑法秩序的整体精神,做具体分析。具体来讲,投保方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都不是单纯的骗取行为;在投保方伙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诈骗保险金的情形下,投保方的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共犯和保险诈骗罪的特征,属于想象竞合。根据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根据法秩序的整体精神,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的,只定保险诈骗罪。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伙同投保方进行诈骗保险金的情形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同时符合保险诈骗罪共犯和贪污罪或职位侵占罪的特征,应根据上述原则,对国家工作人员定贪污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定职务侵占罪。②第六种观点认为,对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案件,应根据角色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定罪。具体来说,投保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勾结时,投保人是核心角色,首先在保险诈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在此限度内,投保人是实行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帮助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另触犯了职务侵占罪或者贪污罪,故需要比较法定刑的轻重。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触犯职务侵占罪,而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职务侵占罪,则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较为合适;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触犯的是贪污罪,而贪污罪的法定刑重于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因此,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贪污罪论处较为合适。反过来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了骗取本单位的财产而与投保人相勾结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核心角色,首先在职务侵占罪或者贪污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在此限度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实行犯,投保人是帮助犯。但由于投保人另触犯了保险诈骗罪,故需要比较法定刑的轻重。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触犯了职务侵占罪,而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职务侵占罪,在此情形下,对投保人以保险诈骗罪论处较为合适;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触犯的是贪污罪,而贪污罪的法定刑重于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在此情形下,对投保人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较为合适。③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然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都不够全面、科学。第一种观点以主犯定性,其所存在的缺陷显而易见。具体表现为:一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是在量刑阶段确定共犯人种类的依据,而不应成为定罪的依据;二是在双方均起主要作用或者对起主要作用的行为本身不能确定罪名时,依主犯便无法处理。④第二种观点忽视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犯罪定性的影响。第三种观点忽视了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时,其特殊身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情形。第四种观点考虑到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对定性的影响,但是没有区别保险诈骗罪和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实行行为的性质、立法精神以及各自法定刑的轻重的影响,实际上是身份决定说的具体化表现。第五种观点虽然看到了实行犯实行行为的性质的根本决定性,同时考虑了刑法的特别规定和法秩序的整体精神,但是没有注意到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时与投保方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情形。第六种观点除了考虑实行犯的犯罪性质外,还考虑各行为人的行为所触犯的罪名,考察共同犯罪中的核心角色,从而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再比较法定刑的轻重,比较全面。但是,核心角色说是以假定在共同犯罪中只存在一个核心角色为前提的,而如何判断是否核心角色较为复杂。如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投保方双方均出于非法占有保险金的目的而互相勾结的,这时判定谁是核心角色就非常困难。⑤因此,基于核心角色本身区分困难,该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故不符合现实需要。
通过比较上述诸观点,笔者更赞成其中第五种观点,但是应该注意到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时与投保方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情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无身份者,二者如果有诈骗保险金的共谋并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则成立保险诈骗罪。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勾结骗取保险金,不论双方分工如何,事实上都只有一个完整的诈骗保险金的行为。这一行为在法律上同时触犯了保险诈骗罪与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两个罪名,只是根据不同罪名,对双方的共犯形态的评价结论不同。如果适用保险诈骗罪,投保人等是实行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是帮助犯;如果适用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保险公司职员是实行犯,投保人等是帮助犯。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等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都不是单纯的骗取行为;投保人等既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犯,又是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共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既是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实行犯,又是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双方的行为都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构成想象竞合犯,可以按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处理。①笔者认为,依据此种方法对行为人的行为定性,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强,而且具有科学性,是可取的。(本文作者:阴建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00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