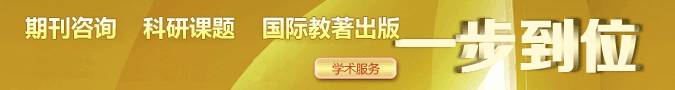表现主义戏剧的误读与反思
“五四”时期,表现主义思潮随同其他各种外国现代派思潮一起进入中国现代文坛,以对现代戏剧领域的影响为最甚。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参与评介表现主义戏剧的学者数以十计,评论者对于表现主义戏剧努力地加以理解和阐释,当然误读和偏颇也明显存在。表现主义戏剧在形式方面的特点早就引起现代评论者的注意,它的灵活多样的技巧不仅拓展了戏剧的表现方式,而且为进入人物灵魂的隐秘领域提供了渠道。正如向培良所说:“自从表现派的剧本在舞台上活跃以来,从前制作剧本的技巧完全被打破了,表现派以非常大胆的自由的手法写他们所爱写的东西,完成许多从前视为不能表现的东西,使剧本之领域侵入更大之方位。”⑨宋春舫、沈西苓、须予、史阙文、洪深、田汉等人纷纷撰文阐说幻觉、人格分裂、象征、变形、梦境等表现主义戏剧技巧,指明该流派具有“反对理智的,偏重幻象”⑩、将“幻觉的场面与现实的场面交错”等特点,剧中人格分裂体现在“其他的人物都只属于主人公自我之一部分的具象化,或自我的反映之姿”;而剧作者则“将他自己对于事物的内心意象或观念,用象征表达出来”“,把自然与现实,放在自己内心的世界,变形而表现之”。田汉已经关注到梦在表现人的隐秘灵魂上所起的作用,认为它“把我们已经忘记的想象的、或情绪的主验重新唤起”。这些对于表现主义戏剧非理性特点的重要阐述,不仅使读者能够具体了解该流派的形式特点,对创作上的借鉴也具有指导意义。田汉、洪深等人就有与其理论评述相谐和的《灵光》、《赵阎王》、《樱花晚宴》等剧作问世,堪称表现主义戏剧在中国的自觉实践。《宋江》、《心曲》、《琳丽》、《春的生日》、《绅董》、《楚灵王》、《文坛幻舞》、《原野》、《春雷》等剧作在幻觉、梦境、象征、变形等形式技巧上也充分汲取了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甘霖,特别是《琳丽》、《心曲》、《赵阎王》、《绅董》、《原野》等剧成为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技巧的成熟之作。
当然,对于表现主义戏剧形式技巧的评述也不尽然是准确的,如洪深的《表现主义的戏剧及其作者》、孙席珍的《表现主义论》、祝秀侠的《大战后的表现主义述评》、史阙文的《表现主义文学的研究》、鸣传的《文学上的表现主义》等文,都阐述了表现主义戏剧的类型化特点,他们认为,其“人物大都是普通的,代表的,如父、母,青衣绅士,黑衣妇人,第一人、第二人这类的角色”,“不主张描写特殊的个性,极其抽象的描出人类的类型”。这些评论仅指出类型化表层上的意义,却未能将其表现人类灵魂本质的特点揭示出来。表现主义者托勒曾言:“在表现主义戏剧中,人物不是无关大局的个人,而是去掉个人的表面特征,经过综合,适用于许多人的一个类型的人物。表现主义剧作家期望通过抽掉人类的外皮,看到他深藏在内部的灵魂。”可见,所谓的“类型化”并非简单地以某个群体、阶层来命名,而是内蕴着以充分表现人物内在灵魂为基础的人学主张。阐释的表层化于创作上的借鉴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现代戏剧史上诸如《病人与医士》中的“病人”、“医士”,《一致》中的“领导者”、“王”、“臣”,《资本轮下的分娩》中的“资本家”、“国家”、“工人群众”、“农民群众”等角色的设置,表面上看似乎实践了表现主义戏剧的类型化主张,但人物形象却因为灵魂的缺失而更像是贴上去的概念化标签,不具有感性的生动性,与真正的“类型化”还有很大的差距。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写实主义的区别是评论界关注的另一重要内容。他们强调表现主义的艺术“脱却外界的印象与自然的模仿……而重视自我,重视主观”,“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反动,灵对于肉的反动”。从反对再现、提倡表现的角度,辨别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写实主义等流派的不同,这是正确的。然而,有些评论者在洞悉这一区别的同时,却把表现主义的内涵无限扩大化,以致将“表现主义”与“表现”、“艺术主观主义”混同为一,导致表现主义与其他流派的混同。这是国人阐释表现主义时最大的谬误。
郭沫若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和《印象与表现》两篇文章,曾十分热情地提倡表现派:“18世纪的罗曼派和最近出现的表现派(Expressionism),他们是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到客观的事物,而自由创造;表现派的作家最反对印象派,他们说他们的艺术是消极的、受动的,他们要主张积极的、主动的艺术。他们便奔的是表现的一条路。”这里的“表现派”,英文为“Expressionism”,指的就是“表现主义”。郭沫若所理解的“表现主义”,显然重在“表现”二字,泛指一切创造的、表现的艺术,此论断固然符合表现主义的特点,但也适合其他现代派的特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表现主义。沈西苓则称“:凡是站在‘艺术主观主义化’的立场上的,都归在表现主义者群。”这显然混同了“表现主义”与“艺术主观主义”,也容易导致表现主义与其他现代派、甚至与浪漫主义的混淆。马鹿对表现主义戏剧的舞台特点作了论述,认为“:表现主义是专尚剧中人物表现的意思,所以不主张考究布景,甚至连演剧台都可以废掉。”这一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把表现人物的“什么”说清楚,也就意味着把表现主义的涵盖范围无限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界对“表现主义”产生的误读,其根源在于未从本质上理解“表现主义”和“表现”的内涵与外延。“表现主义”是一个流派,而“表现”是相对于“再现”而言的美学原则,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杜夫•海纳说:“表现的真实性之所以不以再现的准确性为尺度,就是因为表现并不揭示科学所认识的那种客观化的宇宙,而是主体性所感受到的一个世界的真理。它所说的是一个为了人的世界,一个从内部看到的世界,那种不能复制的世界……一个内心经验过的世界,一个只有情感才能使我们进入的不可模仿的世界。”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包括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等,所表现的对象正是用传统的写实性语言所难以再现的创作主体内心体验过的世界,遵循的都是表现的美学原则,因此,上述的一些评论把“表现主义”解释为“表现”“、艺术主观主义”,是将表现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扩大化,不利于对表现主义乃至表现主义戏剧本质特征的精准把握。现代文学评论界对表现主义的误读,除了评论者自身的原因外,还有可能受到相关译文的影响。斯滨加著、华林一译的《表现主义的文学批评论》(1926)一文,通篇说的都是文学上的表现,而不是表现主义,说明当时文坛把“表现”与“表现主义”混同的现象,在翻译界也出现了。“无限扩大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它看作是无所不包,实际上是在削减甚至取消它区别于其他概念的独特的存在价值”。
如同本文开头所言,表现主义戏剧作为现代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有其特定的精神内涵、表现对象和表现方式。但是,当代的一些评论家仍然把“表达主观感情”、“表现”等词语当成表现主义戏剧的特点,以为表现主义戏剧“强调的是心境和情绪的渲染”,“强调的是作家的主观观念的表现”,注重对人物内心情感的表现,而不追求客观现实的模仿。这些很表面化的模糊界说,同样无法凸显表现主义戏剧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本质特点。还有评论者认为,表现主义戏剧的特征在于对“‘反抗’、‘奋斗’与‘内在精神’的强调”,表现主义戏剧具有“更为鲜明的对抗现实、叛逆传统、反抗权威的战斗气质”,但这些观点未能将斯特林堡和奥尼尔表现人物复杂灵魂的主张囊括在内。况且,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戏剧也描写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而且诸多戏剧流派都注重人物内在精神的阐发,只是所追求的内在精神不同而已。现实主义尊重人在客观世界里的真实性,按照人在现实中的样子来写人;浪漫主义强调主观的真实,往往把个别人物的品格理想化;象征主义戏剧中的很多人物“实际上是某一种东西的象征,甚至是某一种意念、某一种观念的象征物”。而表现主义戏剧写的是类型化的人物,其内在精神是更深刻、更直观地把人类灵魂中永恒的本质揭示出来。虽然,多种流派的交叉融合是世界戏剧发展的趋势,亦是中国戏剧的发展趋势,正如美国戏剧理论家约翰•加斯纳所言:“浪漫主义戏剧终于没有为现实主义作家所废除,现实主义戏剧实际上也没有被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作家以及其他诗剧或想象剧的支持者所置换。纵观我们的整个世纪,剧作的各种风格是彼此碰撞而又相互沟通的。”汲取百家之长,毕竟能促进戏剧风格丰富多样的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去抹煞每一个流派独特的闪光之处。表现主义戏剧在对世界乃至人类灵魂真实性的揭示上具有他种流派难以超越的地方,只有清晰、彻底地了解这一流派及其他流派的根本特点,才能使中国对域外戏剧的借鉴取得实效,走得长远。
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传入中国后,受制于当时的主流文化语境,其涵盖范围在评论者的视野下也发生了变化———德国表现主义戏剧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而斯特林堡和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却被相对忽略。这一偏颇很少为现当代研究者所注意到,它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偏向于关注德国表现主义的剧作家和作品,从剧目、剧情、创作手法到剧作主题都有较系统、集中的介绍。20世纪20—40年代,评论界刊发了四十余篇评介表现主义的文章,一部分文章仅介绍表现主义文艺思潮,并不具体谈到表现主义戏剧,而其他涉及表现主义戏剧的二十余篇文章,则几乎以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品评对象。最早的介绍性文章是春华写于1921年7月的《德国表现派戏剧杰作在东京开演了》,传达了凯泽的表现主义杰作《加莱市民》在东京上演的信息。宋春舫是较早也是影响最大的评介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他的《德国之表现派戏剧》一文较全面地评述了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源流、代表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并在文末翻译了哈辛克列弗的《人类》一剧,这成为中国最早的表现主义戏剧的译作,但该文述及范围仅限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并不如孙庆升所说的“对表现派戏剧作了一次全面的介绍”。而其他如刘大杰的《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主潮》、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余上沅的《最年青的戏剧》等文,都是在论述文学思潮时顺便提及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个别剧目,不作具体分析。这说明在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只是进入了评论者的视野,但尚未被大规模地深入阐述。与之相比,30年代评论表现主义戏剧的文章在数量上虽然与20年代基本持平,且仍然囿于关注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但对该分支的评介在篇幅和深度上都明显加大,涉及的剧作家、作品也增多了。洪深、宋春舫、沈雁冰、清华、史阙文、刘大杰、孙席珍、须予、鸣传、吴朗西等人都撰写长文,于剧情、手法、主题诸方面,专章评论了德国表现主义戏剧,涉及的代表性剧作家和作品覆盖了该分支各个历史阶段,从先驱魏德金德的《青春觉醒》(1891)到早期剧作家索治的《乞丐》(1912)、哈辛克列弗的《儿子》(1914)、《人类》(1914),以至成熟期剧作家凯泽的《加莱市民》(1913)、《从清晨到午夜》(1916)、《珊瑚》(1917)、《煤气厂》(1918),托勒的《转变》(1919)、《群众与人》(1921)等。由此可见,30年代对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评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而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从30年代起,在中国,“表现主义作为文学思潮渐趋淡化乃至消失”,或者“表现主义开始变易并趋向衰微……表现主义的精神特质和艺术倾向受到批判、否定直至消散”。这股思潮实际上在40年代的中国才真正消退。
偏颇现象的另一特征是在评论表现主义戏剧的精神时,集中宣扬的只是反对战争、提倡人道主义、反抗现有社会制度、追求建构理想世界等层面的意义,显然,这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中心意旨更为接近。20年代的众多评论者对表现主义戏剧充满了盛赞之语。宋春舫、沈雁冰认为,表现主义“一方面承认世界万恶,一方面仍欲人类奋斗,以剪除罪恶为目的”,“因为表现主义能够吸收那因大战而始觉醒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于是遂头角峥嵘,光焰万丈”。刘大杰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主潮》中也说“:一到战后,一般人们,都厌恶了战争的罪恶,咒现世界为万恶的大窟,另想建设一理想世界。于是表现主义的作品,风靡当时的文坛。”余上沅的《最年青的戏剧》以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代表作《群众与人》、《儿子》、《煤气厂》等为例,说明那时的戏剧家大部分是主张破坏,全都要和旧的专制阶级时代脱离关系。众多的话语,其内在精神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它们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语境息息相关。这也正是引发我们思索偏颇之构因的关键点。可以说,因为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中找到了精神层面的共鸣,评论界才于两个分支中作出了主观取舍。他们与其说是在介绍一个外来流派,不如说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寻找精神寄托和代言者。“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备受皇权禁锢的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但是,从本质而言,这是一个“暂时失去了思想与现实的双重权威的时期”。当时,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体制瓦解了,两千年来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高度统一的思想体系也被打破了,但是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还未建立起来,代之而起的是军阀割据、内乱四起、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局势。所以,人们获得的自由实质上是一种找不到“根”的自由,处于断层年代的“五四”人的精神状态是在寻找真正的归属,人们祈盼结束战争,建构理想社会制度的愿望特别强烈,这和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基本精神是契合的。茅盾曾言:“表现主义是欧洲大战后处于绝望的德国知识阶级要求出路之心理的表现”,是“处在绝望中的人心的热剌剌地努力要创造的精神……这种心理状况就说明了何以在大战以后的挫败的德国会成为表现主义的最发展的地方。”他对德国表现主义者的评论,深深系根于对“五四”知识分子迷茫彷徨的心路历程的感知和关怀,相当准确地把处在断层中奔突挣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勾勒出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情有独钟了。30年代,中国进入另一个时期,北伐战争的胜利虽结束了国内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接踵而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在这样的背景下,评论界延续20年代的接受倾向,仍然将关注点落在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上,诸多评论者借助德国表现主义以“热烈、雄辩的调子”,面对“威廉二世时代资产阶级的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展开攻击”的精神,称颂表现主义者是“建设理想世界”的使者,是“积极的人类的解放者……不是奔走于革命运动,就是热烈反抗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横暴”,“在恢复欧洲光明灿烂之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力赞扬表现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解放人类方面的功勋,其目的自然是为了给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加油。
由此可见,评介的偏颇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重视德国表现主义戏剧而忽略斯特林堡、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而是以偏概全,于无形之中用“德国表现主义戏剧”来取代“表现主义戏剧”,将表现主义戏剧的全部内涵和精神人为地局限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在此过程中,表现主义戏剧的世界级大师斯特林堡和奥尼尔,却未被纳入或者淡出评论界对于整个表现主义戏剧流派的阐释中,这导致他们无法深得表现主义戏剧这一灵魂艺术的精髓,实质上是对表现主义戏剧流派的一大误读。但是,值得提出的是,20、30年代的文学评论界不乏对斯特林堡和奥尼尔两人的单独评论,只是这些评论很少明确地从表现主义立场去探讨,对其表现主义戏剧或者戏剧中的表现主义特点罕有涉及。孙席珍介绍当时的西方戏剧时,曾提及《到大马士革去》“从肉的世界走向灵的世界,不外乎强固的自我之发露”。这是当时论及斯特林堡表现主义戏剧特点的极少数评论之一。章克标、刘大杰也谈到斯特林堡的戏剧,但其评论属编译之作,无法代表他们的观点。宋春舫认为《去大马士革之路》“是以极端之写实家而正式去受象征主义的洗礼”。吴伴云30年代为译剧《死的舞蹈》所撰序言《史特林堡评传》,也仅说明《梦曲》、《死的舞蹈》具有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比较而言,当时评论奥尼尔的文章较多,至少有六十篇,提及其表现主义戏剧也有十余篇,但是,多数文章仍未点明所评剧目为表现主义戏剧,或即使触及剧目的表现主义特征,却未能冠以“表现主义”之名。余上沅的《今日之美国编剧家阿尼尔》(1927)一文肯定奥尼尔在戏剧上的贡献,指出他的作品中有表现主义剧,但未明确是哪几部。30、40年代如袁昌英的《庄士皇帝与赵阎王》、萧乾的《论奥尼尔》、梦麟的《漫谈奥尼尔》、李曼瑰的《美国剧坛巨星奥尼尔》等文,虽然品评了《琼斯皇》、《大神布朗》、《奇异的插曲》、《毛猿》等剧主人公的内部灵魂活动,但没有分析其表现主义精神所在,更未标明这些剧作是表现主义戏剧。此类评论更多地停留于普泛层面,而非出自对奥尼尔表现主义创作自觉的、有意识的介绍,这表明多数论者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解尚在摸索中,无法凸显他在表现主义戏剧史上的地位。难能可贵的是,尚有少数文章明确评述了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及其特点:如钱歌川的《奥尼尔的生涯及其艺术》、《美国戏剧的演进》两文肯定《琼斯皇》、《毛猿》运用了“将人们的内部生命表现得最显明的表现主义的手法”,带有“象征的、表现主义的倾向”,但此文只涉及上述两剧。曹泰来的《奥尼尔的戏剧》涉及的剧作要广泛得多,确认《琼斯皇》、《毛猿》、《拉撒路笑了》、《奇异的插曲》等一系列剧作属于表现主义戏剧,并指出《琼斯皇》“以八幕连续描摹一个中心幻想”,表现了“琼斯和自己罪孽的挣扎”,准确地阐明了该剧的表现主义精神。除此之外,巩思文的《奥尼尔及其戏剧》(1935)一文,则具体评介了《琼斯皇》、《毛猿》、《大神布朗》、《奇异的插曲》等剧的剧情及其独白、宾白、面具等表现主义手法,确认奥尼尔自1920年后进入表现主义戏剧创作阶段。两年后,巩氏的另一文章《美国戏剧家奥尼尔》(1937),继续分析了上述剧作主人公的表现主义精神。可以说,他从剧情、手法到主题各方面对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戏剧家作了较全面的评述,这也是对其在表现主义戏剧史上地位的直接肯定。综上所述,尽管斯特林堡和奥尼尔并未被当时的中国评论界完全忽略,然而,他们在表现主义戏剧史上的创作主张及应有地位,却没有获得充分的关注和承认,在评价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无法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相媲美。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当年评论界评介西方表现主义戏剧时以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为中心的基本特征。
以评论界的偏颇反观创作界的走向,就会发现,创作界虽也有偏颇,但并未发生类似评论界的全局性倾向,他们对于表现主义戏剧两个分支的借鉴是兼收并蓄的。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剧坛对表现主义戏剧的借鉴有两条路向:一类是追求作品的艺术价值,努力寻求表现对象和表现方式的融合,并且保持了自身独立的艺术品格,如20年代洪深的《赵阎王》(1923)、杨晦的《来客》(1923)、杨骚的《心曲》(1924)、白薇的《琳丽》(1925)、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1929),30、40年代谷剑尘的《绅董》(1930)、曹禺的《原野》(1937)、吴天的《春雷》(1941)等,它们主要接受斯特林堡和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以表现人物隐秘的复杂灵魂为对象;另一类是出于革命政治的需要而借鉴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它们以革命政治题材为主,主题大多表达了变革现实、改造社会制度的愿望,如20年代田汉的《灵光》(1920)、侯曜的《双十梦》(1922)、伯颜的《宋江》(1923)、高成均的《病人与医士》(1925)、高长虹的《人类的脊背》(1926)、白薇的《革命神的受难》(1928)、李白英的《资本轮下的分娩》(1928)、袁昌英的《前方战士》(1928)、田汉的《一致》(1929),30、40年代袁昌英的《文坛幻舞》(1935)、阿英的《洪宣娇》(1941)、洪深的《樱花晚宴》(1941)等。这类剧作的人物形象,多数被阶级或思想观念概念化、图解化,作品每每充斥着革命斗争的口号,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艺术价值。从作品数量看,借鉴德国表现主义的剧作虽然多于借鉴斯特林堡、奥尼尔表现主义的戏剧,但前者几乎都是独幕短剧,后者则多为大中型的多幕剧,其思想意蕴和艺术水准高于前者。由此可见,当时的创作界并未受到评论界的过多影响,他们对斯特林堡和奥尼尔的关注超越于评论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有可能是得益于剧作者自身对于表现主义戏剧原著的阅读与领会。他们对于斯特林堡、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的借鉴,从根本上说是对于这一流派分支艺术魅力的自觉追求。
但是,现代戏剧界借鉴表现主义戏剧的热潮只是短暂的现象,它兴盛于20年代,进入30年代逐渐衰弱,至40年代中期已经消退。因此,表现主义戏剧在中国的创作潮流只能称为兴盛一时,这与当时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如果说“五四”时期,现代戏剧界对于表现主义戏剧的接受既出自对这一流派艺术本身的喜好,又出于社会环境的需要,那么,30年代左翼思潮的到来则冲淡了“五四”以来借鉴现代派戏剧的热潮。左翼联盟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强调,与现代派戏剧的主观性及非理性特点是相斥的,这就促使作家自觉地回归到传统的“写实主义”创作,独尊写实形态,或针砭时弊,或为革命呼风唤雨,观照的往往只是社会生活的表层,而对于呈现主体非理性心理的表现主义戏剧乃至其他现代派戏剧的借鉴自然会中断。白薇的创作演变即为显例。她写于20年代的《琳丽》、《革命神的受难》,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杂糅了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元素;但其30年代的剧作《乐土》、《假洋人》、《姨娘》等,写实主义特点已非常明显。其中,《乐土》是对《革命神的受难》的改编,将原剧富有表现主义特点的类型化、象征化手法消除了,代之以写实性的人物身份,主题也具有很强的革命现实针对性。此外,田汉、杨骚等人也有类似的风格变化。创作界的转向说明了主流文化语境对于剧作者接受包括表现主义戏剧在内的外来现代派戏剧有一定限制,这虽是一种无奈,但并非不可超越。当时,洪深、谷剑尘、曹禺等人仍然坚持对表现主义的创造性借鉴,创作了《狗眼》、《绅董》、《原野》等较成功的剧作。虽然少数作品无法挽回大势所趋,但是它们的存在有力地表明剧作者对艺术独立品格的执著追求可以超越时代主流语境的束缚,显然,作家自身的内因才是决定其创作是否转向的根源。
在接受、认识、借鉴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过程中,只有从接受对象的本体出发,全面了解表现主义戏剧的内涵和本质特点,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借鉴。而从接受主体看,超越文化语境的限制,立足于艺术品格来接受表现主义戏剧,才是根本之途。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域外戏剧流派的精髓,达到日臻成熟的创造境界。如果说托勒和凯泽的表现主义戏剧倾向于为社会寻找出路,那么,斯特林堡和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分支则是在人的灵魂迷宫中寻求出路,无论这样的寻求是否会有结果,应该成为戏剧探索人物复杂灵魂的主要参照系。我们从现代戏剧史上诸如《琳丽》、《心曲》对梦境的细致展现,《赵阎王》、《原野》、《绅董》对“琼斯皇”模式的借鉴,已经可以看出两位表现主义大师留下的深深印记,他们如何“运用最明晰、最经济的戏剧手段……向我们揭示人心中隐藏的深刻矛盾”,如何“有能力把他头脑里所发生的战争以外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种透视人物非理性心理的创作财富理应得到中国当代评论界和创作界的继续关注和深入学习,也势必生长远的滋润与影响。(本文作者:陈达红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30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