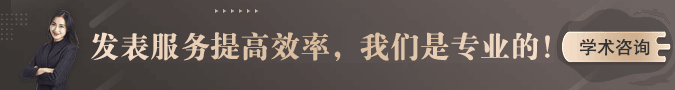喜剧艺术论文:阮大铖戏曲的喜剧艺术探析
本文作者:卢旭 单位: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
决定一部剧作是悲剧还是喜剧,主要应看整部剧作的总体性质和氛围,而阮大铖的四剧不仅全剧整体富于较浓的喜剧氛围,即使就前半部的悲剧情节而言,其情节设计也与《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公认悲剧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从冤案的起因来看,往往缺乏有力的实际证据和必然的逻辑关联。《春灯谜》里,宇文彦只因上错船,并以粉墨敷面,兼之当时水贼海獭皮较为猖獗,便被韦初平误认为水贼,抛下江去。并不糊涂的县丞审案时,明知其中必有隐情,但他为了收取贿赂、向上报功,却仍把宇文彦打入大牢。《双金榜》里,因在皇甫敦寓处搜出了衣巾、黄金,虽然汲嗣源当庭作证、辩驳,蓝廷璋却仍判其流配广东。这些冤案的判定往往极为简单草率,没有有力的实际证据,同时,判案的官吏并非道德或政治上的大奸大恶之徒(《牟尼合》中封其蔀、麻叔谋除外),如韦初平、蓝廷璋都是清官良吏,只是由于一时气恼或是刚愎自用、固执偏见,便将当事人判定有罪。也正因为证据的缺乏、罪责的莫须有,加之判案官吏在人品、道德上的无可指责性,使得主人公所遭受的刑罚并不非常严厉,不至于处以极刑。所以,主人公在蒙冤受屈的过程中并未遭受到彻底“毁灭”的结局,只是受到暂时的困厄,有利于削弱冤案本身的悲剧色彩,实现由逆境向顺境的自然而顺利的过渡。
其次,从主人公面对冤案的态度来看,他们选择的不是正面迎击,而是避走逃遁。《春灯谜》里,宇文彦定罪入狱后,不敢直陈实情,而是遮遮掩掩、瞻前顾后,“本待将真正籍贯名姓供出,恐他解去到那节度使处发落,断是没命的了。故此只得隐下,仍将于俊诡名顶了一名死罪。”《双金榜》里,皇甫敦与莫佽飞海上相会,被人密告官府,他没有立即去直接辩驳来自苗帅府的“飞诬”,而是“何妨死心蹋地,永作波臣”。《燕子笺》里,鲜于佶诬陷霍都梁风月传情、暗通试官,霍都梁也是直接逃奔西川节度使贾南仲幕中。只有《牟尼合》里,封其蔀向麻叔谋诬告萧思远图谋不轨,萧思远曾想过要“我就出头与他抵辨一番,讨个明白,死也不惧”,“猛拼七尺付刑司。便就箯舆,青天湛湛难装砌。做厉鬼咆哮尚可为。”但他随即又听了妻子的劝告后“,改变了姓名衣服,潜避他乡外郡”。因为剧中主人公在蒙受不白之冤后,多较为清醒理智,认为如果自己直面迎击、当场辩驳,不但不能洗脱罪责,反而可能身陷囹圄,以致身首异处。于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改名换姓、潜避异乡。在突如其来的冤狱构陷面前,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直接迎击,而是甘心或无奈地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要么想一死了之,要么就远遁他乡,表现出的是一种书生的软弱气质。
最后,从主人公遭受冤屈的过程来看,其所受苦痛并不是很多,且常有善人的鼎力相助。《春灯谜》里,宇文彦被捕入狱后,幸亏小吏豆卢询殷勤照看、劝慰,使他在狱中免受许多苦楚,还为其洗脱冤狱而多方打探。《双金榜》里,皇甫敦被流配广东后遇见莫佽飞,莫了解详情后深悔连累皇甫生,于是多加庇护。皇甫敦的邻居詹彦道因同情其遭遇,便将其子抚养成人。《燕子笺》里,霍都梁因惧祸而逃奔西川节度使贾难仲幕中,时值安史之乱,而他非但没遭受颠沛流离之苦,反而被贾委以重任。《牟尼合》里,萧思远离家后相继得到芮小二夫妇和达摩的救助,萧子佛珠也得到王僩的解救与令狐頔夫妇的养育。可见,主人公在蒙冤受屈的过程中,不但没有遭受“毁灭”的结局,而且由于诸多善人、贵人在其危难之中伸出援手,使他们所受的痛苦、磨难也并不是很多,这也削弱了悲剧情节的沉重性。
阮大铖四种剧作鲜明的喜剧风格,除了表现为以悲衬喜的总体结构外,还有来自其情节设计的巧妙艺术手法,其中使用最为频繁、最受人称道,同时也最易为人们诟病的技巧是误会与巧合。
误会的发生总要引出种种矛盾的产生或激化,剧中人物为事件的表象所蒙蔽,他们按照各自理所当然的思维逻辑固执地坚持下去,越是争得不可开交,越显出这一争执的无意义和荒谬。巧合是指某些人物、事件凑巧符合某种特定关系,或他们恰好在某方面相同或相似。戏剧是受时空因素限制较大的艺术种类,要求剧作家更为集中、有效地反映纷繁复杂人情世态,运用“巧合”这一艺术手法,便可通过描绘偶然性来揭示必然性。误会、巧合常常并提,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巧合容易引起误会,或者说误会是巧合的结果,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嬗变关系。《春灯谜》里,因半夜起风,宇文行简和韦初平两家的船改变了停泊地点,加之宇文彦和韦影娘在呼唤仆婢归船时,因为“承应”与“春樱”的声音相近,二人错上到对方的船上,于是引发了后来的种种误会,这是由于人物姓名在读音上的接近,而导致的对于不同人物的误认。此外,某些特定事物凑巧都出现在本不属于它们的场合,便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误会,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双金榜》里,莫佽飞趁元宵灯节偷了皇甫敦的衣巾,假扮一书生混入安抚使蓝廷璋府库,盗走龙母宝珠和黄金一锭,弃衣而去,来到皇甫敦寓处,趁他酒醉未醒,留下黄金作为酬谢。蓝廷璋因看到了正巧从衣巾里掉落的书信而知是皇甫敦之物,并在其寓所发现丢失的黄金,由此断定必是皇甫敦偷窃了宝珠。可见,巧合可以导致误会的产生,正因为某些人、事凑巧符合一定的条件或关系,便容易使当事人被这种表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所蒙蔽,于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采取了不适当的行为。
阮大铖的剧作题材多是自出机杼,他以充足的信心和勇气进行艺术虚构,他说自己的《春灯谜》:“其事臆也,于稗官野说无取焉,盖稗野亦臆也,则吾宁吾臆之愈。”[3]5这些构思奇巧的喜剧情节也绝非异想天开、凭空虚构,而是在误会、巧合的情节中,有着严谨、细密的埋伏照应,也就是李渔所说的“密针线”。《春灯谜》第二十六出《吁触》里,宇文彦在狱中撞地自尽未果,“伤面流血”,豆卢询让禁子取来膏药,“禁作将包头捆头,膏药贴生面介”。这一细节似乎只为表明豆卢询对宇文彦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为下文哥哥对面认不出弟弟的巧合、误会埋下伏笔。第二十八出《释累》里,李文义(即宇文彦之兄宇文羲)在提审化名为于俊的宇文彦时,正因为宇文彦脸上贴着膏药,才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同胞兄弟。阮大铖文思严密,不露破绽,充分利用细节上的埋伏照应制造出了种种矛盾、巧合,具有浓烈的喜剧氛围。如王思任所言:“中有十错认,自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至上下伦物无不认也,无不错也。文笋斗缝,巧轴转关,石破天来,峰穷境出。”[4]169韦佩居士认为《燕子笺》也同样“抅局引丝,有伏有应,有详有约,有案有断。即游戏三昧,实御以左、国、龙门家法;而慧心盘肠,蜿纡屈曲,全在筋转脉摇处,别有马迹蛛丝、草蛇灰线之妙。”[5]627
在喜剧中灵活地运用误会和巧合手法是非常必要且有效的,王思任曾言:“天下无可认真,而惟情可认真;天下无有当错,而惟文章不可不错。”[4]170文章需要通过展示“错”的偶然性来揭示情理的必然性,但过于频繁地展现事物的偶然性,整个情节的发展变化全部由偶然性来主导,即误会、巧合运用得过多过滥,偶然性取代了必然性,就会将传奇的新奇性推向极端。《春灯谜》共有“十错认”,误会、巧合几乎成了整个剧情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单是人物改名换姓就有数次。韦影娘改为尹氏女,宇文羲改为李文义,主人公宇文彦更是连续两次更名,先后改为于俊、卢更生。人物更改了名姓,而其实质并未发生变化,外人也不得知晓,这就在名与实、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等方面出现了矛盾,以此制造喜剧效果。但过多、过频的改名换姓会使观众对这种无变化的单调重复感到厌倦,对剧作者熟练运用多种喜剧技巧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使剧作由竭力追求的曲折离奇走向了反面的单调贫乏。张岱在谈到袁于令《合浦珠》时,批评了这种创作倾向:“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6]249阮大铖对于戏曲新奇性的追求本是无可厚非的,其创新独造的勇气和努力也值得借鉴,但有些剧作却走向极端,愈出愈奇,以致达到不顾情理必然性的荒诞不经的地步。
阮大铖的戏剧艺术成就较高,不但精于曲词创作,而且通晓舞台演出艺术特点,他家蓄声伎,亲自排演,“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7]141阮剧浓烈的喜剧氛围很大程度上源于插科打诨的技巧,这种滑稽调笑的穿插可以调节情节冷热气氛,逗观众发笑使其提神醒脑,有些科诨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入故事情节或人物语言中,并非是生硬地插入。
首先,从喜剧语言方面来看,《石巢传奇四种》的诨言依其与剧情及剧中人物的关系疏密,可分两种:一是外交流式诨言,一是内交流式诨言。外交流式诨言主要指人物上场时较为滑稽地自报家门,或对于某些人情、事理的调笑性叙述。这类语言与戏剧内部故事情节关系不大,或单纯为展现人物自身的滑稽性格,或对于人情世态有所讽刺、揭露。从这类诨言往往面向观众表述,易产生表演的“间离效果”,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距离,而观众也可以保持“旁观者”的清醒状态,用较为理智、冷静的态度来评价舞台上的事件,这就容易产生喜剧效果。他这番登场自述是具有间离效果的外向交流式的,展现出一个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大言不惭、诡滑浪荡的性格特点。而且他毫无顾忌地自暴其丑,甚至是以一种自矜、夸耀的态度展示出来,这就使他的登场独白以夸张、滑稽的方式获得了批判和讽刺的艺术效果。内交流式诨言,是指剧中人物在相互对话过程中所涉及的滑稽言语。这类诨言有助于展示人物性格,尤其是净、丑的喜剧性格,还可以调节演出节奏,活跃剧场气氛。“大略曲冷不闹场处,得净、丑间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剧戏眼目。”[1]《牟尼合》第二十九出《塾哄》中,令狐赐与邻家张咬住(丑扮)一起读书,一日两人入馆迟到,当萧思远问及原因时,令狐赐道:“不瞒先生说,学生家母今日诞生,故此来迟。”再问张咬住,张答道:“不瞒先生说,学生家母今日诞生,故此来迟。”萧思远怒道:“胡说,他的母亲今朝诞日,难道恰好都儹在今日?定是说谎,要打。”张咬住辩解道:“学生这蛋,不是他的那诞,是家下养的一只母鸡正在窝里生蛋。我家母亲说,咬住你侵晨空心,且不要馆中去,待母鸡蛋生了,煮与你吃去,是这个蛋。”二人答语一模一样,但丑利用“诞”与“蛋”的谐音双关,构成两重不同的意义,两重意义相互干涉、冲突。在注重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社会里,一个是庄重严肃的母亲生日,一个却是卑俗无聊的母鸡生蛋,丑角的诨言把崇高的精神的东西降格为卑俗的物质的东西,这就使精神与身体、崇高与鄙俗、庄重与油滑、人与物等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事物混淆起来,柏格森认为:“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去的事情都是滑稽的。”[8]34
其次,从滑稽动作来看,阮大铖注意到“科”与“诨”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他在剧作中有不少明确的滑稽动作提示,使人物在表述诨言或唱白的过程中,以滑稽性的动作相配合,取得了极佳的喜剧表演效果。另外,科诨表演也绝非净、丑的专利,“科诨二字,不止为花面而设,通场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诨,外末有外末之科诨,净丑之科诨则其分内事也。然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9]57生、旦、外、末的角色性格具有庄重严肃的特点,一些“恶俗”、“淫亵”的科诨不可能由他们来表演,要想充分发掘各类角色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为全剧制造更浓的喜剧氛围,就需要多为生、旦、外、末设计一些“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的科诨。《春灯谜》第二十五出《湘省》中,宇文行简夫妇(分别由末、老旦扮演)的大儿子宇文羲考中状元,因鸿胪误传名姓,皇帝便钦赐更名李文义,而宇文行简也父以子贵,升了五经博士,改姓为李。宇文夫人对丈夫道:“孩儿头角峥嵘,你也钦赐该姓,真是李牛之子骍且角了。”二人“相笑介”。《论语雍也》有:“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冉雍的父亲是低贱之人,孔子用犁牛比喻冉雍的父亲,认为冉雍虽然出身低微,但他自身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是完全可以摆脱出身的局限而仕进为官、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剧作借“李”、“犁”语音上的相似,构成谐音双关。宇文夫人借冉雍的典故来说明儿子的才华和显贵已超越父亲,并调侃自己丈夫是父凭子贵。这一科诨一方面符合角色末和老旦的性格特点,符合人物出身书香门第的身份和修养特点,另一方面它将谐音双关融入了典故的活用之中,显得含蓄蕴藉,是一个典型的“雅谑”。
最后,单独的科诨笑料固然可令观众解颐,但如果将它们自然融入富于喜剧氛围的情境之中,构成一个在特殊条件下有着相对完整的人物矛盾关系的喜剧场景,这种喜剧气氛会更加浓烈,且可以包含特定的思想意蕴。《春灯谜》第三十一出《闹祠》中,宇文彦来到黄陵庙穿戴起自己原来的衣巾,庙中道士以为鬼魂出现,个个惊惶失措,乱棍打走宇文彦。此前,庙祝师徒以为宇文彦早已不在人世,而宇文彦对此情况毫不知晓,于是矛盾的双方都不了解真实情形,都为假象所蒙蔽,产生了极大的误会,喜剧效果也正由此而产生。庙祝师徒表面上整天与鬼神打交道,而一旦见到“真的鬼魂”,却又极度恐惧,他们在特殊条件下的无意识行动真实地展现了其虚伪、胆怯的本质,这又与他们平时神圣崇高的神职身份形成了较大反差。而宇文彦不明就里、一派无辜,却先被当作盗贼,后被当作鬼魂,最后被一通乱棍打出门外,无辜受屈、狼狈不堪。这一喜剧场景便出现在矛盾双方都抱有极大误会的情况下,展示出他们之间的并非不可调和而是一触即破的喜剧性矛盾,尤其是他们自身性格、经历与现实状态间的矛盾。与之相似的喜剧性场面还有《双金榜》里《廷奸》一出,朝堂之上,皇甫孝绪和詹孝标(即皇甫孝标)互相揭露对方父亲的种种罪案、过失,“嫡亲骨肉,对面却不相认,真是可笑”。
阮大铖的戏剧并非单纯追求曲词奇巧的案头之作,“阮圆海自撰曲本,《燕子笺》、《春灯谜》先出,家伶奏伎竟诩新声。”[10]629他蓄有家伶,亲自排演,对于传奇戏曲的舞台艺术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创作的科诨,能够使剧中角色在举手投足、曲白科介之间都表现出性格鲜明的喜剧特征,还可以调节快慢节奏、冷热气氛,使舞台的喜剧气氛热闹而不粗俗,典雅而不板实,也让观众在诙谐妙趣中达到放松身心、赏心益智的娱乐效果。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86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