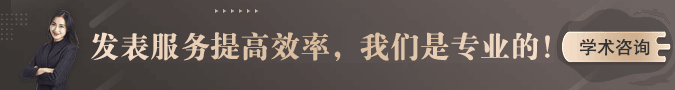宗教语言论文:朗费罗的宗教语言探讨
本文作者:柳士军 单位: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朗费罗在诗歌中常用基督教的语言、比喻、象征探讨人文主义的思想,诗歌倡导的平等互助、爱人爱己、同情弱者的思想隐喻人类对灵魂与精神提升的诉求。然而,一般不具备宗教情怀的读者很难发现诗人作品里隐含的诗化神学。
“宗教是文化的意义,文化是宗教的形式。”[4]42文化与宗教互为表里关系,相互依存,文化的建设者拥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哲学是“真”的,艺术是“美”的,宗教是“善”的;宗教的“神性”与诗歌的“人性”紧密相关,没有诗歌的“人性”,也很难奢谈宗教的“善性”,宗教因其“善”成就了诗歌的“真”与“美”。
伊斯兰教认为,与人为善乃大善。朗费罗诗歌中的“善”既有佛教“善”的因子,也有伊斯兰教“善”的质素,但最主要是基督教的“善”:即“因信称义”。对基督徒来说:顺着神的意思就是为善。耶稣是善的典范:“耶稣对摩西和先知们怀有崇敬之心……因而他是真人。……他大胆地用手、用心宣告那是上帝。从而他,我认为,是历史上唯一了解人的价值的灵魂。”[5]94“因信称义”中的“信”也是指对“惟有耶和华本为善”的信仰。“信”是一种判断权,因为当我们信耶稣或神的时候就交出了对一切的判断权,耶稣就成了我们是否为好人的判断者,所以对于什么是“义”,只能由耶稣给出。[6]朗费罗的诗歌告诉人们,对上帝的顺从是一种美德,是“善”:“那一天就要来了,那时所有人都会看到,上帝对灵魂的恩赐并非是巨大、难以抗拒、独一无二的神圣,而是甜蜜而自然的善良,正如你我的善良,因此它邀你我保持美德,弘扬美德。”[7]92以《明天》为例,朗费罗写道:“上帝啊,我微不足道,可你从未放弃对我的关怀,冬日寒冷的夜晚,你把我找寻,等在我的门口,浑身冰冷湿透。”如同爱默生,在朗费罗的眼中,“信”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善”,是万物的源泉。人的生命和形体都起源于上帝,不能与上帝的意志背道而驰;否则,“事物(将)变得丑恶”。朗费罗的很多作品都流露出他真实的基督教的“善”,即使是他翻译的作品和他的传奇小说描写都暗示了这种宗教思考的习惯,他曾以《基督》命名写了三部曲诗剧:第一部是《神圣的悲剧》,描写基督的时代,象征“希望”;第二部《金色的传说》描写中世纪的故事,象征“信念”;第三部《新英格兰的悲剧》是由殖民地时期两个民间传说组成,象征“慈善”。诗人的宗教话语就是在艺术创作中“我在思想”的“善性”流露。朗费罗将基督教的三大纲领写进诗里,使他的诗歌无处不体现着浓厚的宗教情怀,在这种宗教情怀的感染下,读者达到人类向往的“伟大、神圣、崇高、完美”的超我的艺术审美境界。瑞•帕默博士说:“朗费罗的很多诗歌显示了他对基督教信仰观的赞同,不仅仅是诗歌美学方面,还是诗歌主旨上,基督教思想赋予他的诗歌爱与高尚的灵魂。即使朗费罗在翻译他国的作品依然是根据其宗教的习惯性思维来选材。他的很多诗歌充满了健康的宗教精神,自觉地或者无意识的影响他的思想。宗教的风格是可以模仿的,但是真正的宗教情怀是很难仿冒的。”[3]164人文主义诗人一旦踏进宗教的领域,就会变得伟大、神圣、崇高、完美;人文主义诗歌一旦拥有宗教情怀,就会变得纯真、清新、淡泊、魅力无穷。
基督教人文思想具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质素,纯朴而庄严,幽深而旷远。“爱”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怜悯和救济下层阶级,把积极谋求富贵看成是罪恶;它提倡爱的精神,认为通向天国的道路重要的在于有一颗爱心。朗费罗诗歌中宣传这种“博爱”的思想俯拾皆是,我们仅以《不能丢弃的爱》为例。诗歌描写的是一位富裕的女奴隶主,为基督教“爱”的精神所感动,主动解放了她所有的奴隶。此诗表明朗费罗弘扬的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相爱的思想,宣传一种人文主义宗教伦理观,消解人性中的兽性、非理性,发扬光大人性中的爱。耶稣不仅爱苦难深重的普通人,还以宽厚的态度对待有罪之人,欢迎觉悟来归的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他不嫌弃被社会所鄙视的罪妇和税吏。朗费罗诗歌中的奴隶主散尽家财,觉醒而归,回到博爱的家园,回到信仰的境界。朗费罗对深明大义的部分奴隶主也给予歌颂,在言说他人的同时,正是诗人博爱的人文主义思想在流传。
在朗费罗长诗《海华沙之歌》的结尾,海华沙要求他的人民(印第安人)接受白人的信仰,其实就是基督教“爱”的思想。朗费罗的愿望是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与外来的白种人要互相帮助,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海华沙,愿和平降临于你;愿和平降临于你和你的人民;祈祷和平便获得和平的宽恕;基督的和平,玛丽亚的欣慰”。海华沙离别之前再三嘱咐:“听从他们的金玉良言,听从他们的真理言论。”这是朗费罗对美国文明和世界文明一个最大的贡献:放弃了将战争作为和解民族争端的方式,学习先进的文明,回避军事力量和正面冲突。我们知道种族仇恨和宗教歧视往往是最普遍的引起战争的原因。美国建国后100余年,本土上没有爆发民族之间的战争也说明朗费罗的美好的愿望获得了认可。朗费罗诗歌里表达了对宗教的情感,博爱的思想在他另一首长诗《伊凡吉琳》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当伊凡吉琳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他的丈夫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她谦恭地俯下自己的头,低声说道:“天父啊,谢谢您”。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怨恨,诗人朗费罗完美地表达了伊凡吉琳对命运的诠释,对“博爱”的领悟。《伊凡吉琳》就是耶稣受难的影射,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初期一部分市民的受难史,不仅仅歌颂了伊凡吉琳的真挚的爱情,而且反映了美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其实质是表现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伦理观。在对《伊凡吉琳》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上,诗人参照了《旧约全书》的风格,诗歌呈现的景色完全是清教徒式的;诗的色调也带有寒冬的感觉,与清教徒严峻的眼光相吻合。朗费罗灵巧地展现伊凡吉琳备受责难的特征,以宗教影射表达人文的内涵。接近诗歌的结尾,朗费罗的宗教情怀伺机而发,油然而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肯定伊凡吉琳的自然情感,表达了对人性的赞誉,读者无疑也会被诗人的艺术情怀所带来的欢愉、灵动,以及真、善、美的艺术审美情境而感动。朗费罗诗歌中尊重理性、崇尚自我牺牲与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思想组成了美国文学文化内核的一个重要质素。
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及作品无一不关注死亡与永生的主题。费尔巴哈曾说,倘若世上没有死亡,亦不会有宗教,宗教即诗歌。显然,诗歌的主题离不开死亡,诗歌指明了人的最终的归宿,宗教最终给予人心灵以慰藉。
在经历了人生早期所有痛苦、怀疑和困惑之后,朗费罗最终与自己的人生和信仰达成和解,唯其有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约翰福音》)这样的笃信,他才可以做到“死,归也”这样的超脱,才可能将死亡视为另一个更高存在的永生开始。朗费罗《夕阳金焰》的最后两节如此写道:“人生也一样:到了暮年/衰老似幽冥降落;/天上地下焕发的金焰/也能使天地融合。/和平的洪流中,精灵浮游着,/奋发,欢快,又恬静;/在哪儿从地下进入天上,/灵魂已记不分明。”诗人把死亡写成是和平的,恬静的,甚至是愉悦的,生死浑然一体。诗人对待死亡是这么乐观,这么洒脱,表现了一种颇为旷达的生死观。宗教话语作为文化记忆定格在诗歌的语言、意象、情感中,我们所欠上帝的就是一个死亡,上帝迟早会收回去的,我们不欠平庸什么,所以朗费罗在诗歌中呼吁我们要活得高贵。另外,最能体现朗费罗死亡的宗教观的是他的《收割者与花朵———死亡颂》:“有一个收获的人,他的名字叫死亡/他用了他锋利的镰刀,一口气收获了那些谷子/和那生长其中的花草/但是希望却打破了悲哀,它注视着那收获者的脸/那收获者笑着说/我的主需要这些快乐的花朵/它们是世界宝贵的纪念物,在世上,他也做过儿童。/不带凶残,不带怒气,那天来了那收获的人/他是天使来拜访这碧绿的大地,带走了那些香花。……没有死,似乎死的只是转变/人间的生命乃是天堂的生命的边沿,死的是它的大门。她没有死,我们那可爱的孩子/她进入了那个学校,在那里管理的是基督自己,/我们软弱的保证她不再需要。”诗歌语言明净清丽,纯朴自然,哀婉动人,这种宗教的话语在朗费罗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做到心领神会。这是朗费罗书写的一篇死亡颂,与作者本人的《人生颂》遥相呼应:“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我们能够活得高贵,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诗人鼓励我们面对死亡,振作起来:“对任何命运都要敢于担待/不断进取,不断追求/要善于劳动,善于等待。”“无论是在描写一个孩子的生命刚刚来到人间就离世,还是写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的死亡,或者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撒手人寰,他的诗歌总是绽放出希望和激励光芒。那些不愿意接受亲友故朋离去的人们是多么渴望这种情感的慰藉。这些美丽的真挚的诗歌词语对于那些悲痛欲绝的人们是有帮助的。他没有书写任何悲伤的音符,(对上帝的)怀疑从未穿越他温柔的心空。但是,他能够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有一双先知的眼睛看透生活的孤独,我们坐在他的身边,听他娓娓道来的思想,那些曾令我们沮丧的潮水般的精神情感重新燃起了希望,那是永生的希望!”[3]166朗费罗用诗歌表现自己的宗教体验、宗教理趣,具有强烈的哲理的光芒。诗人使诗歌与宗教一样焕发了神圣的光环,照耀着人类黑暗现实的时空,给人的心灵以希望的温度、高度、亮度、宽度、厚度和纯度。
艾略特认为,文学的伟大性在于只有把宗教精神与宗教感受力包括在内才能使它完满。对于朗费罗而言,宗教是人生心灵解脱的一个重要方式,诗人的宗教话语是升华了宗教含义的皈依体验。当朗费罗肩负起犹如教徒一般的艺术使命的时候,他以宗教精神和宗教感受力来处理复杂的现实经验,如教徒一般有着为艺术而殉道的精神情怀,没有这种精神情怀的抚育,朗费罗就不可能获得高山仰止的名声。
朗费罗宗教思想的产生主要源于美国19世纪的社会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初期的文化可以称为一种宗教文化,它是美国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和社会凝聚力的核心。朗费罗出生成长在宗教气息浓厚的牧师家庭,这样的家庭往往是启蒙知识分子的摇篮。朗费罗自小就耳濡目染了基督教的教义和伦理,并有得天独厚的机会接触到各种神学思想,这不但对其早年的思想有不可估量的塑造作用,同时也为其后来的宗教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朗费罗的弟弟在谈到朗费罗的宗教信仰时说:“宗教贯穿他的生命。他的心是虔诚的,他对生命和死亡的想法基本上是愉快的,有希望的,乐观的。他不在乎其讨论神学,但他认为在世界上和在宇宙中有万能的主宰。”朗费罗的妻子芬尼,也是来自一个唯一神教派教徒的家庭。通过家庭的纽带,宗教话语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影响了朗费罗的诗歌创作。朗费罗的女儿爱丽斯曾经很高兴地告诉她父亲的崇拜者:“她的父亲是出生在唯一神教派教徒的家庭,他的一生从未改变宗教信仰。”朗费罗在《路旁旅店故事集》曾讲述他的宗教信仰:“带着虔诚的步子来到世间/不是要将造物主驱逐/而是为了深入的朝拜造物主/创建一个普通的教会/传播神圣的上帝之爱/满足众多的人类之需”。
诗歌的宗教话语是一种对人类自身意义的探寻,一种虔诚的精神信念,一种深沉的情感诉求。只有对宗教的眷恋,诗人才会具有浓厚的宗教话语。“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8]91朗费罗以宗教话语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以宗教启示论与情感对抗美国建国初期艺术的功利主义、生活的实用主义、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从而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文学成就。阅读朗费罗诗化的宗教话语,他的作品中处处洋溢着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以及彼岸价值的追求,可以感悟作品中那游走在人和神之间的思想指向,我们不妨冒昧借用圣经的语言来评价他:“神看着是好的”。脱离了基督教的信仰、思想和传统,缺乏宗教的话语,读者是无法正确理解和认识人文主义诗人朗费罗的。无论当代自由诗歌如何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变幻,甚至在接受朗费罗的过程中发生重要的误读,朗费罗诗歌中的文化价值和宗教美学依然会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作品仍然是19世纪美国文学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83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