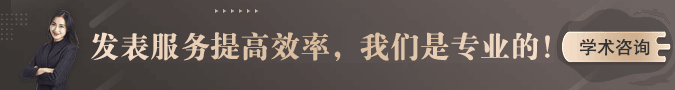文学信仰论文: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反思探讨
本文作者:蔡登秋 单位:三明学院中文系
当大部分楚地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中原文化冲刷得荡然无存的时候,湘西还是一块相对纯净文化之地。所以,在这里楚文化存遗相对完整,并且一些原始文化元素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由于文化土壤的独特性,作家文学创作文化语境亦显得自然独特。历史以来,这里孕育了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沈从文堪称代表。沈从文在他的文学天地中开创性地拓开一个新的文学空间,即湘西世界的文学空间。五四启蒙时期,在焦虑、危机、颓败和失落等复杂的时代情绪冲突中,回归和守望乡土是沈从文那时的创作思想倾向。湘西是一块孑遗着原始性状巫楚文化的“圣土”,是沈从文离开此地后魂牵梦萦的情感寄托,这也正是他一再标榜自己是“乡下人”的原因之一。我们在阅读沈从文作品的时候,不难发现文本所呈现出的湘西文化,大体有两大内容:其一是纯洁中略带着原始味的人情关系;其二是那种古朴略带野性的地方习俗。这两个方面的表达并行不悖,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沈从文独特的湘西文化世界。
沈从文文学作品中民间传统,主要是以湘西民间信仰中的鬼神信仰为主,而这些鬼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名目繁多,种类丰富。我们知道,巫楚文化有好善鬼神的特性,巫术的情结很重。《来凤县志•风俗志》记载:“来凤地僻山深,民杂夷獠,皆缘土司旧俗,习尚朴陋,史称俗喜巫鬼,多淫祀,至今犹有存在。”来凤县今属鄂西,与湘西交界,百姓与湘西相类,好鬼神民俗也是相同。古代长江以南的苗蛮之地,都有崇尚鬼神风俗,就如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卷二所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与湖湘地区同属南方其他地区,也有崇尚鬼神的习俗。如闽地也是多“尚巫信鬼,好淫祠”,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记载:“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语不通。”[2](P22)可见古代的南方的广大地区,人本文化出现相对较中原迟,鬼神信仰浓厚且延续时间长。当中原已进入较为自觉的人文时代,南方诸多地方还较处于神话时代。随着中原文化的南渐,南方很多地方慢慢被中原文化所整合,而僻远的湘西地区保留了相对完好的巫楚文化,所以湘西的鬼神巫术信仰给人印象显得神秘独特,由此也显示了湘西文化现象的独特性。
沈从文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湘西,湘西文化是他的文化经验根基,或者就是他的一种母语经验。在他潜意识中,作为文化内核的民间信仰是他离开湘西后魂牵梦萦的情愫。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鬼神信仰的描述,究其原因,其实是文化母语经验不断复现的结果,这也形成了沈从文文学世界独特的文化景观。
以丰富的民间信仰资源作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
阅读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湘西文化有一种神秘感:这里民间信仰的丰富性和繁杂性,使湘西笼罩在浓厚鬼神氛围中。湘西的土家族、苗族等民间信仰体系的复杂性和种类的多样性,主要是源自于文化的原生性。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成长的沈从文,他文学中民间信仰谱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显然在情理之中。
湘西民众信仰大多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有论者认为这种信仰现象是一种自然拜物教,“由于苗族先民的自我,避让和自主保存才换来了巫楚文化在一定范围内的长久流传。巫楚文化作为自然拜物教文化的遗存,其特点在敬神、信巫、畏鬼。”[3](P178-179)其实他们信仰始终处于自然状态之中,并非仅仅是一种拜物教。不仅如此,“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4](P397)苗族是一个多鬼神信仰的民族,祀奉鬼神的法事种类繁多,据了解这里的法事多达七十余种,主要功能就是用来“祭拜善鬼”、“驱除恶鬼”。这里的崇拜对象多得无法估量,与他们生活相关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崇拜的神灵。如:天王神、土地神、山神、雷神、猎神、龙神、树神、口舌神、飞山神、揭网神、簸箕茶神、楼公楼婆神等等。这些神灵大多是善神,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联系紧密,往往是生产生活的护佑神;但也有所谓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东方鬼、西方鬼等鬼魅,这些信仰对象大多是凶神,它们被称为恶鬼。这里“鬼神的种子,就放在沙坝儿孙们的遗传着的血中了。”[5](P117)因此,这里的“庙宇的发达同巫师的富有,都能给外路人一个颇大的惊愕。”[5](P117)
由此可见湘西的民间信仰浓厚的程度。除鬼神崇拜以外,另外一大信仰谱系就是巫傩信仰。湘西一带自古有“巫作傩戏酬神”的习俗,乾嘉年间,湘西、湘西南的苗族、土家族巫风仍很繁盛。“冰雪官衙吟,千山响竹涛,苗风尚巫卜,边俗竞弓刀。”这首名为《道署雪夜咏怀》的诗,描述了夜闻湘西凤凰巫作法事的联想。[6](P164)清代中叶容美(亦称容阳)的土家族土司诗人田信夫对本地巫傩现象是这样描写的:“山鬼参差迭里歌,家家罗帮截身魔,夜深响彻鸣鸣号,争说邻家唱大傩。”[6]P164)这里巫风兴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湘西的傩祭,晚清时名目繁多并与当地习俗密切结合进行:疾病延医服药之外,惟祈祷是务。父母病则延老者十人,用牲牢以为请命神,谓之打十保护;童子病则延巫为之解熬,名曰扬关;又或以处鬼作崇,于河边井岸用犬羊祭之,谓之打波斯。[7]所以,湘西的巫傩祀神的现象就是常态化生活内容:凡酬愿追魂,不论四季择日延巫祭赛傩神。祭时必设傩王男女二像于庭中,旁列满堂画轴神秘像,愿大者反搭台演傩神戏。[8]由此,湘西地区巫傩风气之甚可见一斑,显然也是本地的一种文化特色。
由于湘西信仰丰富多样,所以庙宇不少,“小小县城里外大型建筑,不是庙宇就是祠堂”[4](P397),据统计这里有:风神庙、火神庙、龙王庙、刘猛将军庙、关帝庙、岳王庙、文昌庙、城隍庙、观音堂、女娲宫、王公祠等五十多处。[9](P17)如此丰富的庙宇孕育了厚重的庙宇文化,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是沈从文写作湘西风俗历史文化时,能够驾轻就熟的一个主要根基。
湘西苗、土家等少数民族的信仰可以归结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巫术崇拜等。湘西信仰的丰富和多样化,给湘西文化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这种神秘性实质上是东方神秘文化的典型。在很多地方已不存在的信仰对象和仪式,湘西却还有这样的“活化石”。所以,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以丰富的信仰对象作为文学主要表达对象,为他的作品笼罩了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鬼神信仰是一大类,大致有以下几种:在小说《哨兵》出现的观音菩萨、巫术还愿、城隍庙、牛头马面、大小无常、天王庙、巫医信仰、大手鬼、大眼睛鬼、死鬼等;在《落伍》中有“角母鬼”;在《神巫之爱》中有尉迟恭、张果老、铁拐李;在《凤凰》中有:狐、虎、蛇、龟等。沈从文的作品中还有一类信仰是巫术,如《凤凰》中有“放蛊”、“落洞”等;在《神巫之爱》中有“巫傩崇拜”;在《病》中有“设坛捉鬼”;在《一个母亲》中有“设坛打醮”求雨。这两种类型的信仰体系大体能够反映湘西信仰状况,从自然社会神明、精灵鬼怪到巫傩崇拜,名目繁多。沈从文除了全方位地对湘西风俗风情进行充分的阐述,也突出了湘西信仰的特异性和复杂性,呈现了湘西文化的神秘性,同时也凸显了湘西民众纯净的心灵与原始的生存状态。
沈从文独特的民间信仰叙事手法
在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中,民间信仰叙事往往是文本叙事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叙事是一种在场的叙事方式。“在这一民俗叙事建构中,被聚焦的民俗事象成为叙述和描写的基本内容,其目的是详细介绍某一民俗事象,其结果是民俗叙事呈现出描述民俗文化学的特征。”[10](P98)这是一种叙事者在场的方式,与叙事对象同时出现,表现信仰仪式的真实性和现场感,那么这种叙事方式也就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直录的方法。如《神巫之爱》中神巫的祈福仪式活动过程与叙事者同时在场,神巫的表演就是叙事者观察到的直接结果。神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叙事者的眼皮下进行着的,都是一系列细致传神的“现场直播”,而不加任何的渲染。这种叙事方式有利于民间信仰仪式过程记录的真实性表达。
另外一种民间信仰叙事方式是信仰叙事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充当故事情节中的主要内容,而只是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有的则是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如《哨兵》中以地方鬼神文化观念作为铺垫,用鬼神信仰来帮助结构故事,作品从谈论鬼的有无、鬼的真实性等入手,引出的沙坝是一个“鬼的种子,就放在沙坝人儿孙们遗传着的血中了”和“庙宇的发达同巫师的富有”[5](P117)的地方,就连“普通一般人治病的方法,得赖灵鬼指示,医生才敢下药”[5](P117),如此地重视鬼神,所以他们的一切处事都与神灵挂上钩了。军人证明自己是否清白得去天王庙“明心”,甚至还有在神灵前“掷筊”判断犯人的生死。由此作了充分的沙坝地方鬼神信仰现状的叙述后,才引出了哨兵轮值夜班过程中对鬼魂一次完整的恐惧经历,鬼神信仰现象成为了发生在沙坝道尹衙门哨兵值夜班恐惧经历的必要条件,这种叙事方式与上述所说的“在场”叙事方式就大相径庭了。
此外,还有一种叙事方式是直接把民间信仰对象和仪式活动作为叙事的内容,也就是直接谈论信仰,全方位地介绍信仰的对象及其存在状况。散文《凤凰》纯粹是以介绍地方巫术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其中关涉了湘西的巫术中“巫蛊”和“落洞”两种信仰。关于“巫蛊”,作者从典籍记载开始,介绍了湘西巫蛊中的名称、蛊人、放蛊的方法、中蛊者的症候、“草蛊婆”的习性、惩治蛊婆“晒草蛊”、蛊人的真相、行巫者的身份与过程等方面;介绍“落洞”(也是女巫的一种,专指在男权社会爱欲遭受压抑,心理畸变行为反常,被世人贬斥的女性[11](P286))也是从落洞的缘起、身份、性质、状态、习性、最后死亡的情况及落洞的解决办法等内容。这种叙事方式是以讲述事实的内容为主,而不是一个故事的叙事;但在这种讲述过程中,也穿插了一些相关的故事,如族长刘俊卿误杀夫人的故事,为落洞习俗的叙述作了铺垫。总之,以介绍信仰对象为内容的文本叙事方式是阐释湘西文化的一种主要方式,从沈从文湘西主题的文本整体上考察,这种叙事方式还大量存在于其他小说和散文中,也是他建构湘西世界文化的主要手段,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沈从文再现了湘西独特的文化状态。
民间信仰的诗化表达是沈从文文化反思的一种方式
沈从文的民间信仰呈现并非一味地表达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严肃性和本原性,更多的是以一种审美性意象表达来诗化民间信仰,这种表达无疑是对严肃的宗教情结和意义的消解,而走向一种诗性的文学诉求和本真自然状态的人性追求。这也是湘西世界具有独特“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主要原因,从而使之蒙上了温柔敦厚的乡土牧歌情调,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诗化的情调。
神灵信仰与爱情结合的表达方式,使民间信仰的严肃性淡化,增加了人情味和朦胧感。如《神巫之爱》把神巫描写成“骄傲如皇帝”的“神之子”,他的“风仪是使所有女人倾倒”,全然是一位让所有姑娘倾心的“情种”,这与现实中神巫庄重的身份有着明显的反差。同时沈从文笔下的民间信仰叙事与民间信仰仪式的严肃性不尽相同,神巫的祈福祀神的过程却变为了示爱和求爱的过程,这无疑是对民间信仰仪式过程的严肃性的一种诗化化。神巫被人认为是一种“绝地通天”的社会角色,这种人能够做到“人神相接”的特殊身份与普通人完全不同,“巫扮成‘神’后,便成具有神灵力量的超人”[6](P336),有诗唱道:“沙锣镗其呜,铜鼓坎其鼓,杂沓如巫觋,缤纷饰猫虎。束腰垂红巾,齐头裹青组。里僚掷叉跳,洞瑶掉臂舞。……我闻教民俗,祭法必师古。容貌束衣冠,揖让严步武。……非类必不歆,失礼非所取。……”[6](P164)诗行中主要内容讲述了苗族、土家族人跳傩祀神的状况,神巫的装束动作行为规范,气氛凝重,体现了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严肃和庄重。而沈从文小说文本中的人神沟通诗意化和人性化,这种叙事的诗化化与现实的差异性完全在于作者的“小说在探索理想的人性形式、关于人的改造的理想时”,“所坚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立场和文化精神”[12](P212)。有意识地把民间信仰仪式过程严肃性进行淡化,追求一种人性和人情的诗意存在。
沈从文对民间信仰进行诗意化的目的是他的文化思考,对于“鬼神”观念的强调,并不是把它置于“科学”的对立面来认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于阐释;不是把它简单地视为一种信仰,而是作为一种娱乐人的性情的文化来对待。小说《凤子》从城市写到乡村,叙述了走进湘西的城市人对鬼神态度的转变:“你前天和我说神在你们这里是不可少的,我不无怀疑,现在可明白了,我自以为是个新人,一个尊重理性反抗迷信的人,平时厌恶和尚,把这两东西外加上一群到庙宇对偶像许愿的角色,总拢来以为简直是一出恶劣不堪的戏文。”[5](P386-387)这里是总爷与城里来老师的对话,在看完傩戏后“老师”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都市现状是“虚伪的象征,保护人类的愚昧,遮饰人类的残忍,更从而增加人类的丑恶”[5](P387)。然而对于湘西百姓来说,“神”是存在的,是“庄严和美丽”的,不过神存在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5](P387)。这种观念就是作家在城市和湘西的对比中产生的。此外,作者还借“老师”之口谈论了神之于“科学”和“政治”的关系,批判性地指出政治的自私、愚昧和屠杀的一面。沈从文对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的思考是独特的,对民间信仰态度并没有与五四时期的反抗迷信和“现实批判”的潮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是采取独特的文化视角自觉反思民间信仰,从中发现人性的纯洁和人情的素朴,发现贴近自然、皈依自然的重要性,从湘西文化的观照中发现“善”和“美”,由此更加深入地对现代文明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与寻根文学中“湘军”的民间信仰描写是不同的,“湘军”所反映的更多趋向于巫楚文化重新发现和传统文化的寻根,而沈从文的立足点更多在于借湘西文化反思现代文明;沈从文的湘西文化呈现也并非是局限于地域情怀中,而是应用对比的思维对未曾受过现代文明浸染的湘西文化进行发掘,这种对比思维恰恰是当时“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现代反思是从湘西文化的反思出发,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所存在不足与缺陷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一点恐怕是沈从文文学思考的独到地方,也是其创作独具魅力的一个原因。
湘西是沈从文魂牵梦萦的故乡,湘西古朴的文化传统是他对现代文化反思的起点,湘西神秘的民间信仰现象是他文化反思的内核。沈从文通过民间信仰叙事构建了一个区别于现代文明的湘西文化图景,呈现了一个朦胧的、诗意的、神秘的湘西人的精神世界,他也随之成为一位难得的自然纯朴文化的精神家园守望者。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78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