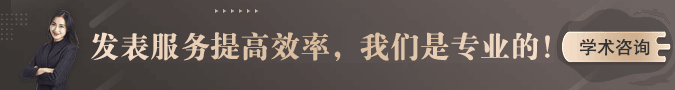小说形式论文:曹文轩小说的形式美感研究
本文作者:蔡常山 单位:燕山大学
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莱夫•贝尔于十九世纪末首次提出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假设是“艺术的追求并不是形式的模仿,而是形式的创新;艺术也不是对现实生活中情感的反映,它所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情感’”[2]。贝尔所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中的“意味”实际上就是指某种特殊的“情感”,而“有意味的形式”则是指审美的形式,这也是贝尔美学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文学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审美情感方面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文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形式”是文学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与技法,是作者寄托其内在审美情感的手段。绝大多数作家都对“形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作品中每一个人物、每一项安排的背后都隐藏着审美的意味,曹文轩小说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形式”美感正是如此。
悲剧精神
曹文轩的作品历来以凝重、优美而著称,其作品的内在力度和美感大多来自作者的悲剧意识。可以说,作者强烈的审美情感就是对于悲剧精神的高度认同,这种悲剧感是作者由内而外的一种抒发,并非刻意为之。看过《红瓦》的朋友一定对这段林冰的心理独白有很深的印象“我让我的心变得悲凉,当我独自坐在河边或门槛上时,便可品尝这份情感,它让鼻子酸酸的、让心酸酸的、让眼泪汩汩的流进嘴里,让我可以仔细品尝泪水的咸味”[3]。主人公对于这种“悲凉情感”的品尝,目的是为了获取形式上的快感,从而得到一种无法从他人处获取的满足与慰藉。
悲剧除了可以让人产生浅层悲伤外,还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就有关于“悲剧可以陶冶性情,可以让观众产生无害快感”的描述。对于古典主义者而言,悲剧往往是人生意义更为厚重、深刻的体现,他们将美通过痛苦这一形式进行表现,虽然看似矛盾,却是一种到达深刻情感的有效途径。无论是《草房子》中家道中落最后只剩五枚鸭蛋的杜小康,还是《青铜葵花》里因意外而使房子化为灰烬的青狗父子,都会使读者的内心因为悲剧感而得到净化。失败是悲剧的外衣,但是其内涵依旧是美,这些痛苦和磨难启示、教养着少年们,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残酷而美丽的仪式。
贵族趣味
我国古典主义作家们拥有者浓厚的“贵族意识”,这是一种西方绅士趣味和传统士大夫趣味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其家庭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农户人家”,称之为“乡间贵族”无疑是更加贴切的[7]。虽然成长于江苏盐城的农村地区,但曹文轩的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属于“乡间贵族”,所以高洪波在对曹文轩进行评价时,使用了“灵魂忧郁、文字优美、姿态优雅的‘三优’作家”的说法,目的就是对其“贵族”形象进行全面描绘[8]。
曹文轩自己从来没有掩饰对于贵族文化的推崇,他认为“贵族文化并不是指某一个阶级的文化,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追求的境界、高度、趣味和哲学化和诗化的生活方式”[9]。这里所说的境界、高度、趣味和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够被品味到的“姿态”,是其审美情感的寄托。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曹文轩通过“节制”和“洁癖”对自己的“贵族趣味”进行了充分表现。
(一)节制曹文轩认为,在面对各种不幸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冷静的神情,所以文学作品也不应对痛苦进行过分的夸张。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曹文轩对于美学是独特理念就是为其融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有节制的美更加符合他对于“大美”的向往和追求。理智的、节制的情感是大多数“京派”作家的创作理念,沈从文曾经说过“伟大而神圣的悲哀并不体现在鲜血和眼泪上,作家要竭力避免浮于表面的热情”[10]。例如,《边城》中翠翠的高贵就体现在她的等待和沉默当中。当青铜和葵花面对奶奶逝去时,当艾雯面对丈夫被杀时,当桑桑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的命运使,作者并没有让他们哭天抢地,而是用了一声叹息、一阵清风这样的降格方式进行处理,使人物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表现出一种高贵的从容。
(二)洁癖.曹文轩曾经坦言自己的作品是有洁癖的,在他的文章中,那些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即便是面对很难做到干净的境遇,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于干净的追求。例如,马水清的奶奶虽然瘫痪在床三十余载,但是对于清洗的讲究却让“一个垂死老人的房间不仅没有难闻的气味,反而飘出淡淡的清香”;青铜奶奶的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一年四季都用清水洗濯自己”;艾雯虽然是油麻地中学的老师,但却有着使用干净的杯子和窗帘并且要求学生剪指甲这些与乡野人民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惯。在古典主义者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种贵族式的高傲与矜持,他们倾向于有节制的情感,其目的是超越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生,构建一种可供欣赏的高贵的人性模式,使自己活得“寄情”的满足感。
语言嗜好
曹文轩认为,作为“语言的艺术品”,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和可供审美的资格,相对于形象思维而言,文学语言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进行审美活动[11]。为此他曾经感慨到“作家在写出富有意境的文字时,心中该充满多么美好的感觉”,由此可见,语言是曹文轩形式嗜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典主义者们大多注重语言的作用,他们内心深处的文体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指引着他们的文体试验,而那些试验成功的人则被冠以“文学家”的桂冠。例如,沈从文就一再主张“只有对文字进行组织,才能使它们具备光和色”[12]。这里所说的组织体现在具体技巧上,就是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别具一格的语言表达手法。
在技巧的运用上,曹文轩首先表现出了古典主义者的一贯做派,即通过使用象征、通感等描写方式让小说具备与散文和诗相同的气质:“他拄着拐棍,站在斑驳的雪地里,仿佛灵魂已经飘零。”[14]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们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升华为审美作品,“文学性”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存在与文学的艺术形式构建当中,更表现在对语言形式进行操作时产生的审美效果当中[15]。曹文轩成功的利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陌生”语言形成了一种直达读者内心深处的审美效果,而这种语言的“陌生化”转变则是通过词语组合、修辞等技巧来实现的。
在意象的选择上,曹文轩擅长通过月光、芦苇荡、红瓦、白栅栏、大河、山谷等构建诗化的世界,诗从语言开始,又在语言终止,仅凭这种意象的组合就可以产生一种无穷的美感,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就是这种作用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曹文轩小说中的“形式”美感离不开这些意象,百合花与紫烟、青铜葵花与父亲、柿子树与马水清母亲、苦艾与秦大奶奶、蓝花与夏莲香、鸽子与桑桑、野菊花与纸月……这些意象与人物的特征间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使它们最终成为人物的代表符号。
结语
曹文轩的小说在创作上继承了古典主义的做派,在形式上实践了自身对于悲剧精神、贵族趣味、语言嗜好的追求,在精神上悲天悯人、坚守高雅、关注灵魂、强调大美。这些独特的格调虽然使其作品更显厚重,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略显突兀的抒情、过于繁复的笔力,都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性、和谐型和简洁性,对于读者原本流畅的审美心理也是一种阻碍。另外,曹文轩在很多时候似乎过于倾向于“形式”美感,非但自身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而且还为了避免读者无法对其进行领悟而着力过多,破坏了作品中自然天成的美感。
虽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要承认,曹文轩是一个理智、真诚的小说家,他并没有因为对于“形式”的过分追求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是将创作中心放在了优美的精神内涵的塑造上,这也是他能够摆脱形式的束缚,使创作更具思想深度和唯美特征。与此同时,曹文轩也没有拘泥于对于生活真实的模仿,一直坚持对于超越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尽管超越有限,但是追求永恒。当我们对这种尝试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后,方能了解曹文轩对于“形式”美感的不懈追求。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78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