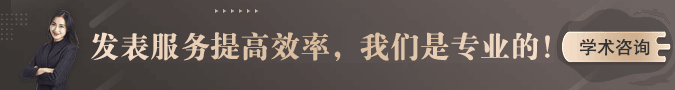英美诗歌论文:英美诗歌中存在主义解析
本文作者:逯阳 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
宗教与自由的艰难选择
罗塞蒂的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描写信仰、受难与禁欲等宗教主题的。对宗教的眷恋,使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比如她在《圣灰星期三》中写道:“耶稣,我爱你吗?你的爱太遥远,我够不着,她躲在天堂的光里。”[4]在这首诗中罗塞蒂反复地吟唱“天堂”,希望身后能升入天堂,但又担心自己得不到上帝的眷顾。罗塞蒂的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其实是对现实存在不满的反映,一种寄希望于来世的表现。通过诗歌,她在反复质问耶稣的爱为何离人如此遥远。可见,罗塞蒂对耶稣已经产生了怀疑,这不是一个普通教徒所能做到的。站在耶稣面前的罗塞蒂,俨然已具有了存在主义觉醒意识。在另一首名为《修道院门槛》的诗歌中,罗塞蒂借用“修道院门槛”这一意象,象征性地表达了自己面对宗教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心理。这也说明了罗塞蒂并非是一个“洁白无暇”的修女,她也有强烈的个人理想和对自由的渴望。“自由哲学”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思想。“我命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5]罗塞蒂在诗歌中对自由的呐喊是她萌发存在主义意识的表现。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人对自己行为的自由选择是人的本性。人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狄金森眼中的存在也有类似的特点,在她看来存在应该是摆脱依附、自由选择的存在。可是,狄金森对宗教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排斥,而是同样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她生活在有着浓郁宗教氛围的新英格兰。在其家乡阿默斯特小镇,加尔文教统治着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所有人都被要求将灵魂奉献给耶稣。狄金森质疑宗教观点和神学的价值观。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和罗塞蒂相似,狄金森也要面对宗教与自由的艰难选择。一方面,她顶住了宗教压力,终生没有成为教徒;而另一方面,在她的内心深处又为自己冒犯上帝而具有了一种负罪感。她在诗中写道:“我不放你走,除非你为我祝福”。这正是她与上帝关系的真实写照。诗人的自我永远处于抗争、搏击的状态,而这抗争不仅是为了远离信仰,同时也是为了接近上帝。在《我死时听到一只苍蝇的嗡嗡声》一诗中,诗人通过模仿死者弥留之际意识逐渐涣散的过程,以考证来世的确定性及上帝存在的真实性,也反映了她对宗教的矛盾心理。
爱情诗里的入世哲学
尽管罗塞蒂已经是一位具有了存在主义觉醒意识的教徒。但她的日常生活、诗歌创作,乃至谈婚论嫁,还是要受到上帝存在的约束和影响。年轻时的罗塞蒂长相甜美,常为其兄拉斐尔前派诗人、画家但丁•罗塞蒂做模特。18岁时,她爱上了画家詹姆士•科林逊并与他订婚,但因为科林逊信奉的是天主教,与英国国教的教义相互冲突,所以两年后罗塞蒂解除了婚约。1862年,她又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学者查尔斯•凯利,后又因凯利是无神论者终使两人劳燕分飞。此后,她还一度爱上了有妇之夫威廉姆•司各特,但结果也是有缘无分。
罗塞蒂通过诗歌述说着自己失败的爱情,在表达了对爱情失望的同时也反映出自己缺乏行动力的入世表现。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决定和体现的,而不是由上帝掌握和安排的。情感的创伤让罗塞蒂的诗歌带上了浓重的忧郁和悲哀的情调。《第一日》是罗塞蒂的一首哀婉感人的十四行诗“:我多么希望自己还记得你我邂逅的第一日,第一时,第一刻,它或是灿烂如夏或是暗淡如冬,我只能如此说。”[6]在该诗中,诗人抒发了自己急切地想找回与爱人第一次相会的那份记忆。却又不能不为自己年少无知不懂得珍惜而懊悔不已。在面对宗教与爱情的艰难抉择中,成年后的她依旧是无可奈何。她在《想念》中写道“:请想念我吧,当我已经不在———不在这里,在远方,寂静的田园;当你已不能握住我的手腕,握住了我的手,我欲去又徘徊。”[7]可以看出,罗塞蒂对于爱情始终保持了一种被动的姿态。她渴望被记住,被怀念,甚至希望被再一次握住双手。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即“入世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思想鼓励人行动,尤其是把人置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状态下,并以绝对自由的事实性来强加于人,使其处于孤立无援又不得不行动的人生悬崖之巅,人必须要行动。”[8]站在爱情的世界里,罗塞蒂虽然孤立无援,却用另外一种方式采取了行动。她在诗歌创作中直白地道出了自己爱的心声,迈出了“入世”的步子,突破了宗教的禁锢。
与罗塞蒂相似,狄金森也曾经历过几次失败的爱情,这也是导致她隐居及终生未嫁的主要原因。虽然狄金森思考的是入世的问题,但采取的态度则是出世的回避。学者们认为,狄金森先后与沃兹沃斯、希金森、罗德等人有过感情纠葛。1854年,狄金森在费城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英俊潇洒的已婚牧师沃兹沃斯并深深地爱上了他。迪金森的一些诗歌和书信都是见证这份爱情的有力证据。甚至可以说沃兹沃斯是触发狄金森诗歌灵感的缪斯,因为她们交往的这几年恰好是狄金森写诗最多的年份。然而,沃兹沃斯已有妻儿,并且身为牧师。在爱情和宗教法度的抉择面前,狄金森选择了后者。1860年,狄金森在爱情诗《但愿我是,你的夏季》中写到对沃兹沃斯的思念:“但愿我是,你的夏季,/当夏季的日子播翅飞去!/我依旧是你耳边的音乐,当夜莺和黄鹂精疲力竭。/为你开花,逃出墓地,/让我的花开得成行成列!/请采撷我吧———秋牡丹———/你的花———永远是你的!”这首诗比喻贴切,正是狄金森内心的真实写照。
与罗塞蒂一样,狄金森爱的行动也同样只是通过诗歌创作来展示的。相比之下,狄金森的爱情诗更加充满激情。比如《暴风雨夜》:“暴风雨夜!暴风雨夜!/我若和你同在一起,/暴风雨夜就是/豪奢的喜悦!/风,无能为力———/心,已在港内———/罗盘,不必!/海图,不必!/泛舟在伊甸园———/啊,海!/但愿我能,今夜,/泊在你的水域!”这首诗描写了暴风雨夜,一对恋人心中却是豪奢的喜悦。在拉丁文中“luxury”有“lust”(强烈的性欲)的意思,所以,这首诗就是表达诗人对其爱人狂野的爱。对爱和幸福的强烈渴望让诗歌中的她穿越了层层风雨,到达了幸福的港湾。这种对爱情大胆、露骨的描写更体现了诗人对宗教的蔑视和对真我存在的追求。
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意识
死亡对存在主义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海德格尔说过,“畏”,是对死的体验。而死作为此在之本质,并不是停止呼吸或停止思维的那一刻,而是伴随着人的一生,无时不在的心理体验[9]。因此,存在是向死而生的存在。只有当人读懂了死,才能真正领悟生的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将死亡看作是自在存在,一种不需要理论观念陈述自然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存在主义对待死亡的总体原则是直面死亡。
罗塞蒂一生身体羸弱,健康欠佳,感情生活又多挫折,晚年更是孤单寂寞,疾病缠身。因此,她钟爱离群索居的生活,在诵经祈祷中独自陷入冥思玄想。对“死亡”的关注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她的一系列与死亡相关的诗都表现了诗人对死亡的深刻感悟:死亡是独立存在,不依赖他物,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比如在《歌》中,罗塞蒂指出“当生命逝去时,不需要爱人用悲歌来哀悼,不需要爱人用玫瑰和翠柏来纪念。只要绿草相伴,只要有雨水和露珠儿的滋润”。这首诗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在诗人的眼里,生命如同绿草,柔弱却顽强,死亡也不过是绿草的枯黄,是大自然的必然轮回。有一生就必有一死。在诗人看来死更是新生的黎明,它是生的一部分。对死亡的深刻感悟使诗人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各种悲哀,克服恐惧、坦然面对死亡、超越死亡。诗人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意识在这首诗里表述得淋漓尽致。
与罗塞蒂相比,狄金森对死亡的感悟也毫不逊色。狄金森对死亡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她一生创作的1775首诗歌中,有600多首是以死亡为题材的。她从生者和死者两个角度来描写死亡。有时,她还把死亡拟人化,让死亡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说来也怪,狄金森常常在写诗之前就摆出了一副已经死去了的姿态,也许这是她在对自己的死亡进行大胆想象和预测吧?她不知不觉地把未来加以无限制的延伸,把死看作是对未来之图景的一种透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种人超越了现在,并达到了真正的自我,从而在这未来之图中认识到一种“永恒的生活”[10]。比如在《我的河在向你奔来》一诗中她写道:“我的河在向你奔来———欢迎么?蓝色的海!哦,慈祥的海啊———我的河在等候回答———我将从僻陋的源头带给你一条条溪流———说啊,接住我,海。”在这首诗中,诗人把人生比作河流,把死亡比作河流归海,河流必然会流向大海。河流从无到有,直到淹没在海洋中。这与存在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人存在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一直在向着死亡推进。人存在最后归结于空无,因为人存在必然会走向死亡,这是无法逃脱的。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待死亡的淡定心态。
对于迪金森来说,死亡也仅仅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并不是什么让人忧伤的事情。死亡不能阻止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反而激发了她对人生的思考。死亡是来世的必经阶段,精神的救赎要以肉体的毁灭为条件,活着的人不可能了解死后的秘密,依附于肉体之中的自我也看不见来世的光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两位诗人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存在主义意识。但在程度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别:狄金森的存在主义意识几乎冲破了宗教观念的束缚;而罗塞蒂则无法摆脱宗教对其思想的影响,让自己的存在意识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尽管如此,两位诗人敢于寻找自我的勇气,以及向死而生的人生感悟却是一致的。她们的诗歌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一种参透人生之后的大彻大悟的境界。这也是她们之间最大的共性。尽管长期生活在相对幽闭的状态下,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们对世间万物的洞察和对人生的品味。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78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