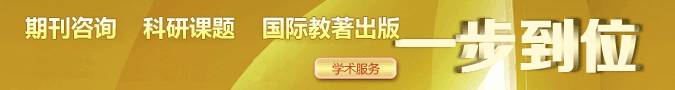王安忆作品中的乡土世界
本文作者:宝毅平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相对于发展迅速的城市来说,乡村的步调总是缓慢的。然而乡村的生活散漫却绝不拖沓,悠闲而又认真,在这缓慢的形式与节奏里,蕴含的是浓厚的人情味。乡里人都是健谈的、热情的,路上遇见的乡里乡亲是总要叫些什么才能开口的,他们不像城里人那样门镜里看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固守着古老而朴素的民间道德和生活习惯,王安忆以她对乡村生活的感动和理解,将这些被人们日渐忽视的人情温暖与礼仪道德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京派作家眼里看来,乡土世界就是人性的一方净土,是人类生存的美好家园,它是皈依也是救赎。在这里,人性不曾受到污染,坚守着自然而本真的状态,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温情,那是一股由内而外的温暖情怀,发自内心的真诚,眼泪和微笑都不掺杂任何杂质,那么清澈透明。这些美与温暖也都出现在王安忆的乡土小说里,并使这些小说就像是一首首乡村牧歌,散发出诗意与温情,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寄托。
《上种红菱下种藕》就是这样一首关于乡土中国的挽歌。在这里王安忆借用中国水墨画的笔法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充满野趣和诗意的江南水乡图,也正是这种和谐的环境孕育了那里人们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合乎人性的伦理法则和朴素美好的人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其言行举止都总是循着“礼”与“情”的标准而进行,亲切而又不木讷,认真却绝不做作。
在小说里表现最深的是顾老师与老友的交往,尤其是老友作画的情景更是把江南水乡古朴雅致的生活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为了女儿的画廊顺利开业,顾老师带着礼物去拜访多年未见的老友画几幅荷花图,来为女儿的画廊打开门面。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和礼仪,走亲访友需要携带礼物,那是人之常情,而顾老师带的礼物很有江南水乡的地方特色:一坛花雕酒,四封云片糕,一方火腿,一个竹制的笔架和毛筒,一幅顾老师自己写的“竹”字,既实惠又有品味。而老友作画的情景更是蕴含着一种自然、健康、优雅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这是一个70多岁的老者,头发花白,声音洪亮,皮肤发出桐油的光泽。作画之前,先要喝上半斤黄酒,然后研墨取笔,运气挥毫,转瞬之间,四幅荷花图,一气呵成,让观者在四幅画里看尽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荷花。这荷花图在别人是千金难求的,而老人却分文不取地将它送给老友,为的只是一个“情”字。在作画与赠画之间,作者挖掘和捕捉日常生活中闪烁的美感、蕴涵的丰富人文色彩的生活场景,赞美了宁静雅致江南水乡所熏陶出的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这里的人们没有什么利益的算计,更没有功利的目的,一切的行动都有真情的存在。
《上种红菱下种藕》里的人情是朴实的、真诚的,没有什么甜言蜜语,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和爱护。秧宝宝是寄住在李老师家里的房客,但却被当做家庭的一分子看待的,这个家里的人无论是强势的闪闪,还是和蔼的李老师或者温暖的陆国慎,全都悉心地呵护照料秧宝宝,并且懂得去维护孩子特有的自尊和小心思,谨守着对孩子的承诺。尤其是陆国慎和秧宝宝这对忘年交间的友情或者说亲情,虽是淡淡的甚至有时是别扭的,却是打动人的。这种人情的温暖、人性的善良在而今是太珍贵、难得,尤其是在城市生活里。那几个住在楼上的东北房客和闪闪一家也不过是普通邻里,却在回老家以后热心地寄来刨花工艺品,这份热心是只有农民身上才容易见到的,他们总是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想办法回报的。还有那个看守老屋的年迈的公公,不辞辛苦地送来瓜秧上结的第一个葫芦,送给回到沈溇的秧宝宝一篮土鸡蛋,这些都是乡民们固守的礼节和道德传统,因其是细节的、琐屑的,才更加令人感动。这种人情与人性的美好是作家所追求和赞美的,也是她所向往的精神家园和人间乐土。
王安忆称颂的乡民们所具有的人性美,尤其表现在女性身上。在《姊妹们》这篇小说里写到这样一件事:“那年我回上海,她(小辫子)从这年的猪肉里专为我留下一刀,等我回来,天天到庄口大路上望我,而我那时的心思早不在我们庄,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告诉我,小辫子留给我的肉坏了。”这份姐妹情深的等候和关爱,是多么令人感动和难以忘怀。在王安忆的意识里,乡村是相对于热闹繁华的都市而存在的,乡村里的“一切都准乎自然,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在乡间所继承的悠久淳朴的民风民俗,处处显示着真、善、美的和谐、自然的画面,这与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忙碌的生活使城市里的人们省略了太多生活的过程,这个人造的环境迫使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效率与利润,它是太理性了。而农村却是感性的、审美化的世界,这份宁静安逸也使乡村有了一种梦的唯美,王安忆就是以这种美抗拒都市里日益膨胀的物欲和道德的沦丧,从而表达她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情的冷漠与疏离、人性的扭曲与变态的拒斥。
人性的自由与美好是京派作家追求的最高准则,在新时代里王安忆能够退出城市,而以精致的艺术描写人生的朴实,站在乡土的立场上,从乡村内部来打量乡村文明,去描写普通人身上所散发出的美的气质和美的感动。可能因其是一个乡村的外来者和城市知识者的双重身份,这种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使她的乡村书写闪现出冷静与客观,使王安忆在小说里把乡村生活美化了,也使她笔下的乡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形而上思考的乡村,是作家充满知性和理性趣味的乡村”。京派作家汪曾祺曾说过:“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王安忆在这个缺乏审美的时代担起了发现美、传播美的责任,像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一样去歌颂存在于乡间的那种人情美和人性美,继承京派作家所崇尚的“一种爱与美的新宗教”,让读者在现代生活的冷漠隔绝匆忙中,重温那一份美与温暖,用她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还存在的美和精神寄托的有限空间。
王安忆笔下的乡村并不像京派文人那样扮演故乡的角色,它们或是作家插队时曾停留过的,或是旅途中经过的,也有纪实与虚构相交融的,其中最特别的还是在城市边缘中存在的乡村生活。她以独特而敏锐观察力,发现了这个由异乡人所建筑的特殊的乡村,它并不因其生活水平的落后而受到作家的鄙弃,而是凭借它自身那种永不改变的美的光采,而得到作者的重视。
王安忆是一个不断寻找的作家,在她重新审视乡村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平淡而普通的生活中寻找到生命的情景和形式。她通过富萍这样的生活于城市而又未遗失乡民精神特质的移民形象,来表达她对日益物质化、世俗化的上海的批判与否定,表达她对勤劳健康、自尊自爱的人生的向往与追求,从而使得她的移民书写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审美追求和人文关怀。这也是她乡土小说的特别之处。在小说《富萍》里,体现了京派所赞扬的那种“诚实劳动与生计的庶民美学以及和谐的生命状态”。④小说描写了隔离在上海市区之外的棚户区闸北与梅家桥,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虽在几辈以前就从乡村奔到城市谋求生计,但却仍保留着乡民骨子里固有的热情和善良。这一点可以从富萍第一次到闸北找寻多年不见的舅舅这件事看出。舅舅是富萍在上海这个陌生的地方唯一能想到的最亲的人,在潜意识里她想要找到舅舅,几次长时间的游走,富萍终于来到了舅舅居住的地方。小说里这样描写富萍找人的过程:“这就是人们说的,闸北,东火车站,旱桥底下,舅舅住的地方。可是,这片棚户那么大,而且密密匝匝,找一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她看见底下,屋檐之间的狭缝里,有个女人在晾晒洗好的衣服,然后,走进去,不见了。眼面前,尽是屋顶的黑瓦,间有一些水泥的平台,凸出在黑瓦之上。黑瓦,一直连绵到天边。然而,这一大片棚户,就像一张大网,它们互相联系。富萍问了第一个人。有没有一个叫孙达亮的男人。第一个人虽然不认识孙达亮,但他很负责地将她引荐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将她引荐给第三个人。他们很有信心地将富萍这样接力棒似地传著,相信她一定能传到地方。富萍身不由己地被传给一个又一个人,有的是一个老人,有的是一个妇女。他们都说着富萍耳熟的乡音,富萍甚至能辨别,是在她们家东边的那个县份,还是西边那个县份。他们不像奶奶那样,带了上海腔的。富萍跟了带她的人,从狭窄的巷道里穿过去。有的敞开的门里,正在吃饭,一眼看见有陌生人来,便端了饭碗走出来问:找哪家的?带富萍的人告诉说找谁家,他们便一同歪了头想,想,然后提议说问谁谁谁去。于是,便一起去找那个谁谁谁。这些房屋大都是砖砌的墙,有的还用竹篱笆围个巴掌大的院子,种些瓜豆,藤攀上来,挂在篱笆上,就有一股草木和砖瓦的气息。又叫爽利的阳光一晒,更加蓬勃。地是泥地,有时会有一段砖铺的甬道,或者一方水泥地坪,中间立着一根自来水龙头。富萍渐渐走进了这片棚户的腹地,她已经记不清被传到第几个人了,她甚至还在其中一个人家中吃了一碗青菜烂面。最终,人们将她引到了孙达亮家。其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放早学的孩子呼啸着穿了过来。”这个接力赛一样的寻人事件花费了那么久的时间,却没有人嫌麻烦,这份执着与热心是只有乡民才能真正做到的,他们从不怕麻烦,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
王安忆在描写生活在这里的从事低下肮脏的工作的底层劳动者时,让人们看到了这些普通百姓的自尊与自爱、勤劳与宽容。“见过他们的船吗?那才叫一尘不染,红漆的床、柜、地板、板壁墙,每天都刷洗一遍。后舱里是垃圾,用帆布遮住,边和角都拉严实了系牢,不漏一丝缝。那气味,还是很重。苍蝇成群结团地随了船走。可是前舱和甲板上,却干净极了。矮桌子、小板凳,直接在河里刷过的,手脚也是随时洗,不穿鞋赤了脚,在舱里走来走去。要是回家,那更是大洗特洗,大晒特晒。岸上的人都嫌船上的人,说他们吃苍蝇下饭,其实船上人最干净了,最容不得腌臜。“”这里的营生,因为杂和低下,难免会给人腌臜的印象。可是,当了解了,便会知道他们一点不腌臜。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杂芜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他们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这些做着各种营生的人们,并不在乎城里人(上海人)的白眼和鄙视,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尊,而是他们比城里人更懂得生活艰辛与生命的价值。在他们的意识里可能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因为他们清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们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踏实实地做事做人,不投机不钻营。他们都是最务实、最踏实的,没有城里人的自以为是和贪婪冷酷。捡拾垃圾虽是脏的、累的,但却给了他们生活的保障,是他们的祖辈在背井离乡时的倚靠,所以他们尊重这份营生。
这些城市里的异乡人用勤劳的付出养家糊口,同时也支持这城市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存在现代文明的城市才能光鲜亮丽整洁。可是他们绝不会去炫耀自己的功劳,无论这份辛劳有没有人去肯定或者称赞,他们都不曾改变丝毫,他们一直保持着农民的那份任劳任怨的憨厚。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被挤压的人们,才是最热爱生活、最懂得生活的人。他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份生计,骨子里永远保留着祖辈留传下来的强大的生命力,不求人亦不自卑。在那些杂芜琐碎的营生下面,蕴含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在这些异乡人的生活里,王安忆所传达给人的是一种淡泊、宁静、乐观的生活态度,她展现的是一种淳朴、和谐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她所描绘的城市里的乡村生活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它率性而为不被束缚,安静和乐没有纷争,尤其是那股向上的、不服输的劲头,更透出中国农民不变的顽强拼搏的力,那是我们民族的象征。
一种新文明的出现与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来传统文化与文明的遗弃甚至毁灭。当王安忆正以深情的目光、怀着温暖的感情回望记忆里的乡村时,都市文明的巨大阴影已经悄然地投射到乡村这片静寂的土地上。旷野的微风失去了往日的酣畅,传统乡村所特有的宁静、和谐、安闲之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渐渐地丧失,在金钱的诱惑下,乡村文明正一步步走向毁灭与崩溃的边缘,因为乡里人的舍弃,也因为城市的挤压。面对这种美与文明的流逝,让作者对乡村的未来充满了深深忧虑,促使王安忆于2001年创作了《上种红菱下种藕》。
小说以9岁女孩秧宝宝的行迹为中心,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叙事:一方面,展示了江南水乡清新幽美的风景、热情纯朴的民风和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对乡土中国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冲击和压力下的裂变、萎缩表现出无奈和忧伤。较之从前的乡村叙事来说,作者的感情明显复杂得多。小说里有几处表现乡村的传统风俗与民间技艺面临失传的无奈与忧伤。小说里写到一次陆国慎带着秧宝宝和蒋芽儿回娘家时,她母亲招待这两个小客人的吃食:“每人泡一大碗‘风消’———用柴灶,锅里不能有一点油星,稻草烧锅,糯米粉调成又稀又筋的浆,悬着,只在烧热的锅底一沾,立即壳起一层锅巴,消薄消保掰碎后,盛在碗里,加上白糖,滚水一冲,滋养得很。现如今,柴灶少了,会做‘风消’的人也少了,小一点的孩子,都有没听说过的。”再如妹囡送给李老师家的各式糕点:“李老师打开荸荠篮盖,果然是各色年糕,便招两个孩子过来看。有一种绿色的糕,拿到鼻前嗅嗅,有一股荠菜的清香。李老师说,这其实是艾果糕,原先是在清明时分,用艾和米粉做成,现在季节不对,采不到艾,就换作荠菜干。篮中又有一种褐色糕,则是用干菜做成,也是艾果糕一类的。再有,雪白的糕中掺有松仁,李老师告诉说,这种糕叫做樊江松子糕。因为在绍兴东边,皋埠镇边上一个极小的镇子,樊江,最盛产。在此基础上,妹囡又发展了嵌瓜子,嵌葡萄干,各种开头点缀其中,花色各异,香味也各异。又有一种松花色的团子,本名为‘松花馍粢’,里面有馅儿,一是芝麻白糖,一是细豆沙。这此都是讲得上名堂的,另外,还有没名目的:赤豆色的,苔条色的,枣色的,菊花色的;长的,方的,扁的,团的。李老师不由说:妹囡何苦开影楼呢?不如开糕团店了!这其中的好多色,早已经失传,她居然还会蒸。李老师各色挑一块,用张干净报纸包了,让蒋芽儿带回去。又挑了少许几样,拿进厨房上笼蒸起。”像这些传统美食有很多都面临失传的危险了。现在太多的年轻人都痴迷于肯德基、麦当劳等西式快餐,而对这些有悠久历史积淀的传统美食都没什么兴趣。这也使得这些传统技艺后继乏人,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这篇小说里,王安忆借用中国水墨画的笔法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充满野趣和诗意的江南水乡图。正是这种和谐的环境孕育了水乡人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合乎人性的伦理法则和朴素美好的人性,就像小说里所写到的华舍和沈溇。沈溇对于秧宝宝来说就像农场对斯嘉丽一样是她力量的源泉,那里有她的根与魂。老屋就像是秧宝宝生命力的血脉一样,每一次回归,都是一次生命的体验,即使离开再久,也永远有家的气息。可是时间的流逝、岁月的侵蚀,老屋终究是残损了,支撑不了多久了。这最后的休憩之地、养伤之所也将被掩埋,忙碌奔波的人们再也没有退路了。小说里尤其令人气愤和同情的是公公的悲惨遭遇。农村与农村人挡不住城市文明对自己土地与生活的侵蚀,却又麻木地观看着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将死的心愿被怎样的践踏。“人们绕过老屋,从两座低矮的院墙之间穿过去,再顺了一条田埂走一段,来到了公公的自留地。这是一块旱地,大约有二分,种了些毛豆。因为人力不济,毛豆长得不好。稀稀拉拉的豆柯里边,石块砌了一个方坑,半边的上方,两片石板架成一个屋脊。这就是公公为自己造的阴穴。人们指点给两位干部看,两位干部戏谑地说:这阴穴也忒简陋了,魂灵也关不牢的。人们便告诉道:虽然简陋,可公公却是用心用意,专程请了石匠来,凿了石方,放下,接缝,才造好没几日,看,凿痕新得很呢!两位干部说:要是新造的,就更错了,县里老早立法保护耕地,废除土葬,满墙张贴的都是:让得三分地,留给子孙耕。难道看不见?人们说:公家都造坟山,为何不让给子孙耕?两位干部说:那是山地,不是耕地。人们就说:现在你们不是来了吗?来得及给子孙耕的!大家还都朝后站站,看那两人怎么动手。”一阵纷乱过后人群散去了,“别人家的门里都飘出饭菜的香,惟有老屋,沉寂着,没一丝动静。”公公的辛酸与抗拒无人可解,只有秧宝宝可怜公公,为他哭了。因为孩子总是敏感的,虽说不清楚却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伤害与压抑,也只有她懂得公公那倔强的歌唱:“买的个溇,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豆,河石勘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大儿子又卖红菱又卖藕,二儿子卖葱韭,三儿子打藤头,大媳妇赶市上街走,二媳妇挑水浇菜跑河头,三媳妇劈柴扫地管灶头……这平直的歌调里,拼力挣着一股劲”,这股鱼死网破的劲儿让秧宝宝害怕。可是公公的惨剧却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秧宝宝怕听怕见又无力阻止的,她只有可怜公公。而王安忆在这篇小说里所给予的对农村文明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忧伤、害怕和无奈。这里太小了,小得无以抗击所谓的文明。“(华舍镇)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的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也许不久的将来秧宝宝重归故里却真的无法再找见沈溇,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人总是需要那个精神的家园和生命的根的。
王安忆曾经这样评论这场现代文明对城市与乡村的破坏“:在《上种红菱下种藕》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小镇,渐渐在现代化的强大模式中崩溃、瓦解,这大约就是现代化崇拜的力量。在这强劲的冲击下,大城市似乎还有一些抵抗,而小的、弱的,像乡镇这样的地方,便不堪一击。它们容量比较小,必须在有节制的消长交替中方可保持平衡。眼看宽直的道路从它旖旎的曲线上辗过,混凝土覆盖柔软的水分充盈的土地,同时,暴富的神话风传在勤劳忠诚的农人耳目间,真是感到心疼。我完全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来取代这迅速消解的生活。在这力量面前,文学忒虚无了,我只能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⑤这个世界用美打动人,同时也让人心酸。这种心酸正如沈从文在小说中为那片充满原始神秘色彩的湘西世界,也开始受到堕落的都市文明侵蚀而谱写的一曲曲挽歌和乡村牧歌。王安忆乡土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个物欲横流、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带着对美好人性和悠久文化的担忧与思考,去呈现那些即将失去的美和悄然行进的异样生活。沈从文曾对城市进行过这样一番解析与批判:“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城市人)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⑥城市的堕落正慢慢地侵蚀着美丽乡村,也同化着生活其间的质朴善良的乡民。正直朴素的人情美正在逐渐堕落之中,而乡人们却毫无察觉,一心追慕着城里人的生活。小镇、乡村正慢慢地被年轻的一代有意或无意的甩在身后,故乡似乎变成了遥远的记忆,模糊了、淡却了。曾经坚信的只要辛勤劳作就会有好收成的朴实的真理,也被新的生活和现代化以各种名义摧毁了。闪闪的聪明、友人的帮助、家人的齐心终究没有挽回闪闪画廊的命运,向外走的人流使华舍这个小镇愈发地凄凉。我们为文明与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真的值得吗?
王安忆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和美丽的乡村,同时也痛心地揭示这些美的流失和遗弃,这是一记警钟。在各国都加紧软实力建设的今天,文化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力和精神力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和民间技艺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是非常严峻的,我们需要某种程度的回归和不能回避的自省。所以说王安忆的这些反映乡土的小说的意义是深刻而又极其必要的,它显示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文化批判的标准。我们应该庆幸有这样的作家存在。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71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