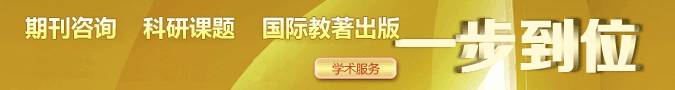李健吾对莫式喜剧的借鉴
本文作者:徐欢颜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1936年1月,李健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以身作则》这出三幕喜剧,属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辑。他在书中标注了“后记”的写作日期:1936年1月10日,由此推想这部喜剧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后记所署的时间之前。李健吾晚年在其自传中,提到《以身作则》在重庆和上海的演出情况,却没有交代此剧的写作背景。[4]1935年8月,李健吾离京赴沪,任上海暨南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除去上课之外,李健吾平时深居简出,伏案写作。[5]很有可能《以身作则》创作于他定居上海之后。这个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并不复杂:地点发生在华北某县城内,一位地方乡绅徐守清有一子一女,他经常以道学教条和封建伦理来要求子女。一位前来县城驻扎的年轻营长方义生爱上了徐守清的女儿玉贞小姐,在马夫宝善的帮助下,假装成医生混入徐家。王婆介绍了一位年轻寡妇张妈给徐家做佣人,满口仁义道德的徐守清对她垂涎三尺,但最终张妈宁愿选择马夫宝善,也不选择这个虚伪的前清举人。方义生的身份最后被徐守清的外甥揭穿,徐守清不得已答应了他和自己女儿的婚事,但要求方义生处罚马夫宝善50军棍。
1937年4月,李健吾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三幕喜剧《新学究》,这一剧作属于“文学丛刊”的第4辑。李健吾既没有写作前言后记,在此后的各种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过这部喜剧,甚至在1981年写作的自传中也讳莫如深。徐士瑚认为《新学究》的写作时间是在1937年1月,[6]徐士瑚和李健吾是山西同乡,又是清华时期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因此即使在徐士瑚并未给出理由的情况下,这一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王为民、祁忠写作的李健吾评传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由于《新学究》引起了清华某位教授的猜忌,所以李健吾失去了回母校任教的机会,所以才举家南迁上海。[7]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新学究》的创作时间当在1935年8月李健吾南迁之前,可能还早于《以身作则》的写作。这位“清华某教授”,在唐振常看来,是吴宓(雨僧)先生。他说:此事(指毛彦文嫁给熊希龄一事)大伤先生之心,更感孤独。先生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从而嘲讽之。先生确乎有新学究之气,但我以为做此事有失忠厚之道,更非先生所应为。1946年,在上海我偶然对李健吾先生言及此意,李先生仍不无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嘲弄老师的痛苦,实在是并不了解老师。[8]
鉴于李健吾在公开场合一直对此剧保持缄默,所以唐振常的说法也有待考证。但不管《以身作则》和《新学究》孰先孰后,都被研究者当作“莫氏喜剧”来看待。作家师陀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1937年9月,李健吾和他在李家书房的谈话,谈话是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杜工部和元明戏曲等众多书籍的包围中进行的。[9]由此可见,1937年左右,莫里哀喜剧在李健吾书房是占据一席之地的。李健吾还在1935年就天津南开新剧团演出的《财狂》一剧发表了《L’Avare的第四幕第七场》的评论文章,而《财狂》恰恰就是戏剧家曹禺对莫里哀喜剧《吝啬鬼》(L’Avare)的中国式编译。由此证明在1935-1937年之间,李健吾对于莫里哀喜剧是非常熟谙的。
《新学究》是李健吾以高级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一部喜剧。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某大学附近,主要人物是一个自作多情的迂阔的中年教授康如水。他当初拿钱送谢淑仪出国留学,为了等她回来结婚,竟和跟随他15年的发妻离婚。但是谢淑仪并不爱康如水,她爱的是与她同船回国的冯显利。冯显利与康如水是老朋友,但他并不知道谢淑仪就是康如水朝思暮想的意中人。同事孟序功夫妇为冯显利和谢淑仪接风,邀请康如水参加。康如水本来打算趁机机会向朋友们宣布他与谢淑仪结婚的消息,但最后才发现谢淑仪并不爱他,她最终选择了与冯显利结婚。这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喜剧出版后相当受欢迎,1937年4月初版,5月旋即再版。
在40年代孤岛困守期间,李健吾又创作了《青春》,这是一个农村题材的爱情故事。观众反响并不很好,读者徐光灿认为《青春》里面最后一幕的大团圆,显然是一种生硬的凑合,这类悲剧,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故事。但李健吾在回复徐光灿的信中说,他原是把《青春》当作喜剧写的。他还辩解说,喜剧,尤其是高级喜剧,往往和悲剧为邻,它让人在笑后感到悲哀,不由不坠入思考;这种笑,才有韵味;这种笑,不仅仅一笑了之,往往倒是真正的悲剧。人世或者由于制度的缺陷,或者由于性格的缺陷,往往形成一种错误,悲剧家把它们看成是悲剧,喜剧家把它们看成是喜剧。莫里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些特殊的造诣。[10]这出喜剧在当时的上海孤岛沦陷区并未引起太多重视,但到了50年代宣传新婚姻法的时候,却机缘巧合被改编为评剧《小女婿》,接着政策的东风演遍大江南北,风靡一时。
从以上对于李健吾喜剧创作的简要辨析中可以看出,李健吾在30-40年代创作的4部喜剧,均或多或少与莫里哀喜剧有些关联。其中《新学究》与《以身作则》两部剧作更是鲜明地体现出莫里哀喜剧的影响。
李健吾在《以身作则》和《新学究》中模仿莫里哀喜剧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从这两部喜剧最基本的故事情节上就可以比较出来。实际上,这段法文出自《丈夫学堂》第1幕第4场,而非李健吾所标示的第1幕第6场。中译文如下:一个女人受到了监视,就起了一半外心,丈夫或者父亲爱发脾气,永远成全情人的好事。当然,这种表面的相似过于明显,但李健吾这两个喜剧的故事情节,都有一个或几个略隐略现的摹本。《以身作则》与李健吾192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故事情节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大兵怎样通过巧计来逼使父亲同意女儿的婚事,这是李健吾创作中存在的相当有趣的喜剧作品与小说作品的互文性再现。《以身作则》中方义生扮作医生去会玉贞小姐的情节还与莫里哀的喜剧《爱情是医生》类似,都是恋人装扮成医生,借看病之机谈情说爱,最终喜结良缘。而《以身作则》中马夫宝善耍诡计、最后遭棒打的故事情节和《司卡班的诡计》又有雷同之处,都是给青年出巧计赢得爱情的忠心仆人最终都会受到顽固封建的老主人的棒打。《新学究》的故事情节则与莫里哀的风俗喜剧《愤世嫉俗》有类似的地方:都是偏执的不为社会习俗所容的男主角在爱情角逐中落败,发表种种奇怪的人生哲学和奇谈怪论。这些相似之处给阅读者带来非常奇妙的似曾相识之感,但并不抹杀李健吾喜剧在情节上的创造性,作家是将各种情节类型揉碎之后进行了重新组合和变形。况且莫里哀喜剧本身在故事情节上也是非常类似的,将莫里哀喜剧与李健吾喜剧区别开来的不是情节,而是人物的性格,因为只有典型的性格才是喜剧创造的关键。
《以身作则》中的徐守清是一个丧失了全部现实感的喜剧人物。尽管时发表生了巨变,但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以往的世界中。他蜷缩在道学之中,用儒家的经典话语代替本真的生活语言,前清举人早已不复存在的优越感遮蔽了他看清现实的眼睛。对于脱离时代的虚伪的守旧者,时代带给他重重的挫败:他的女儿要离他而去,他的儿子也绝不会继承他的衣钵,而那位张妈宁愿跟马夫走也不选择他这位堂堂的举人。李健吾通过道学与人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刻画出“假道学”这一性格内在的虚弱和虚假,揭示了现代性因素战胜不合理的传统因素的必然性。《新学究》中康如水的性格是完全流动的,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这种流动性突出表现在他对于女性人物的狂热追求上。他刚刚还在向自己的梦中情人谢淑仪求爱,遭遇挫败后一转眼的功夫就跪倒在已婚女士孟太太的脚下;他刚刚责骂完自己的恋人忘恩负义,掉头又会凑上去摇尾乞怜。但流动性只是其性格的表面状态,在性格深层实际上还存在着传统的稳定性:康如水主张婚姻与恋爱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有他自己可以享有,女人只能“纯洁、贞节,从一而终”;康教授尽管把女人奉为“高贵的诗神”、“清纯透明的诗之材料”,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专制褊狭的男性中心论者。因此康如水这个大学里的“新”派教授骨子里仍然是一个“老牌儿的学究”。
李健吾抓住“五四”以后社会风俗中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冲突,在冲突中塑造旧派或新派的人物,创造出20世纪30年代社会独有的典型性格。但这种性格却利用了中西极为相似的喜剧情节,在模仿中进行创造。
李健吾还借鉴了莫里哀的喜剧形式。莫里哀喜剧是古典主义喜剧,一般而言都是遵守“三一律”的。在《以身作则》和《新学究》中,也完全遵守了时间、地点、行动的“三个统一”。《以身作则》的时间:第一幕是某日早晨十时,第二幕是一小时以后,第三幕是再一小时以后。地点是:华北某县城内。行动是马夫宝善以种种诡计揭穿前清举人的虚伪面目,使年轻男女终成眷属。《新学究》的行动统一,即康如水等待多年要与谢淑仪结婚的迷梦破灭了;地点统一,即某大学附近的康家与赵家;时间统一,即星期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吃茶点时。两个剧本在形式上都严格遵守了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原则。李健吾在《以身作则》的后记中说:“我梦想去抓住属于中国的一切,完美无间地放进一个舶来的造型的形体。”[11]这个“舶来的造型”,可能是指话剧,也可能是指古典主义“三一律”,但无论如何,他的喜剧创作目标是很明确的,即借助西洋的外壳,使用中国的材料,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
李健吾对于莫里哀喜剧的模仿毕竟是表层的,他的喜剧创作成功之处更在于成功地吸取了莫里哀喜剧的精神。在他的《新学究》中,通过主人公冯显利之口表达了作者本人对于人生喜剧和悲剧的看法:人生是一出喜戏,还是一出悲剧?是一出悲剧的话,什么东西做成它的悲剧呢?你得承认,一个人欢喜的时候总比悲哀的时候少,就在欢喜的时候,马上接着的也许就是一个伤心的伤心。我们不敢凝定思想。一凝定,我们就明白自己多空虚了。真实的只有悲哀的永长的情绪。[12]67你知道,顶高的喜剧也就是悲剧。[12]69
莫里哀喜剧“内悲外喜”的特色,焦菊隐早在20年代就已经总结过了,李健吾也非常认同这一点,认为喜剧,尤其是高级喜剧,往往和悲剧相邻。他在30年代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最高的喜剧不是环境的凑合,往往是人物的分析”。[13]而这种人物的分析,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表现。20年代的焦菊隐转引法国批评家圣驳夫评价莫里哀的话说:“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30年代,在对《吝啬鬼》的分析中,李健吾认为中国文学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于创造性格的淡漠,对于故事兴趣的浓郁”。而中国传统戏剧的主要问题也正在于此,单纯“注重故事的离合,不用人物主宰进行”的结果,使它“缺少深刻的人性的波澜”,因此即使偶尔成就“片段的美好”,但总体上却往往难以达到艺术的胜境。[14]在李健吾30年代的表述中,“人性的共同精神”、“普遍的人性”、“深广的人性”、“人性的普遍情绪”,这些都是反复在作家评论文章中出现的概念。在《以身作则》中,他也写道:我爱广大的自然和其中活动的各不相同的人性。在这些活动里面,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我最感兴趣也最动衷肠的,便是深植于我四周的固有的品德。隔着现代五光十色的变动,我先想捞拾一把那最隐晦也最鲜明的传统的特征。[11]1
李健吾对于莫里哀的“自然”是这样解释的,“尊重自然(不是风景,而是人性naturehumaine,而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真实,是和莫里哀的唯物观点分不开的。这也正是同样尊重自然,然而他和古典主义理论家在领会问题上,根本分歧所在,自然对莫里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本来面目,属于外在,属于形象,‘照自然描画’等于我们今天常常说起的‘表现现实’;艺术家必须正确观察社会现象,在艺术上做出正确的表现。但是对于莫里哀,自然不止于是一种形象存在,所以,尊重自然的客观存在,不仅由于他有形象的一面,而且也因为他有精神的一面。”(李健吾《战斗的莫里哀》,见中央戏剧学院国书馆馆藏油印稿)这种对于“自然”(人性、社会生活)和人性精神的热爱,使得李健吾在创作中希图揭示30年代社会中人性与社会变动的矛盾与冲突。
他进一步解释《以身作则》这部喜剧的创作意旨和塑造人物的原因:人性需要相当的限制,然而这相当的限制,却不应扩展成为帝王式的规律。道德是人性向上的坦白的流露,一种无在而无不在的精神饱满作用,却不就是道学。道学将礼和人生分而为二,形成互相攘夺统治权的丑态。这美丽的丑态,又乃喜剧视同己出的天下。《以身作则》证明人性不可遏抑的潜伏的力量。有一种人把虚伪的存在当作力量,忘记他尚有一个真我,不知不觉,渐渐出卖自己。我同情他的失败,因为他那样牢不可拔,据有一个无以撼动的后天的生命。这就是我为什么创造徐守清那样一个人物,代他道歉,同时帮他要求一个可能的原谅。[11]2-3这一大段表述,区分了道学和道德,认为道学的丑态正是喜剧表现的对象。这和莫里哀喜剧倾向于表现人性弱点、缺陷是一致的。而且他对于徐守清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正符合莫里哀对于喜剧任务的界定:“喜剧只是精美的诗,通过意味隽永的教训,指摘人的过失。”
此外,李健吾对于喜剧作品,还有这样的期许,认为“作品应该建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11]2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将现代中国的一切放在舶来的造型中,将莫里哀喜剧的形式和精神借用到自己的喜剧创作中,传达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性和人类共通的情感。
总之,李健吾在自己的现代喜剧创作中,通过与莫里哀喜剧情节和形式的表层相似,寻求精神内质的沟通与契合。他的《以身作则》和《新学究》这两部中国现代喜剧,不是单纯的“莫氏喜剧”,而是地道的“李氏喜剧”:将莫里哀的美学影响化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没有闹剧的肤浅,又不及莫里哀喜剧的沉重,而是“内悲外喜”,深挖人性,是个性化的、民族化的喜剧艺术。
但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后,李健吾对于莫里哀喜剧的借鉴和超越并未能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延续下来。50年代初期,李健吾创作了活报剧《美帝暴行图》中的两出:一为《战争贩子》,一为《伪君子》。为了抗美援朝的政治背景而紧急赶制的《伪君子》与30年代的《以身作则》、《新学究》相比,艺术上显得粗糙之极。在李健吾的《伪君子》剧作中,大而空的政治宣传话语代替了细致入微的性格描绘,急就章的剧作忽略了对于人性的开掘,导致他的《伪君子》在形式和语言上都有明显的模仿莫里哀《伪君子》的痕迹,却缺乏莫里哀喜剧深刻的人性力量。李健吾的《伪君子》创作,是抽离了莫里哀喜剧精神之后的肤浅模仿,形在神失,是其后期喜剧创作中的败笔。而形肖神聚的“莫氏喜剧”,正好是李健吾20世纪30-40年代现代喜剧的点睛妙笔,使得中国现代喜剧摆脱了初创期的草率和粗略,开始逐渐过渡为相对成熟的中国现代喜剧。
通过对李健吾现代喜剧创作的考察,可以看出莫里哀与李健吾喜剧创作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莫里哀喜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李健吾的喜剧创作,莫里哀惯用的情节和形式为李健吾的奇思妙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舶来的造型”,但李健吾被称为“莫氏喜剧”的那些现代喜剧作品,其中凸显出来的精神气质和包蕴着的美学内涵,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70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