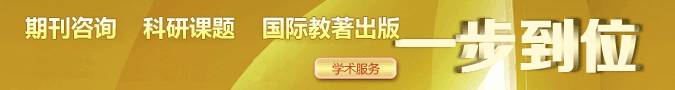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探讨
本文作者:李春雨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文化系
小说家张恨水等通常都被拒之“京派”之外,而那些与“京”没什么亲密关系的一干外乡人,诸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林徽因、师陀、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却被认作是“京派”。这自然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京派到底是不是一个流派?京派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老舍凭什么不是京派作家?当然也有反过来说老舍进了京派反而地位很尴尬,成了一个异类1等等。京派的论争,命名只是表面现象,更为本质的是京派作家的审美追求。其实,关于京派命名的问题并不难说清。如果把京派的思想主张与审美追求分为两个层面的话,那么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追求的是质朴优雅、田园牧歌、古典沉郁的精英文化的一路;而老舍等人则追求的是北京底层市民的精神气质,着力展现的是老北京的风情民俗,使用的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分,则前者是京派,后者是京味;不分,就是大京派,从周作人到老舍都是。
此外,京派的起止时间也不是以在北京或离开北京为标准判定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原来活跃于京津等地的“北方文学者”四散全国各地,其中一大批成员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重建“京派文化的大本营”2,延续京派的创作风格与文化理想,有不少学者提出,抗战爆发后,京派虽然离开了北京,但京派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延续到战时的西南联大及朱光潜等任教的成都大学、武汉大学等,文学新人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可谓京派的后起之秀3。近年来,更有学者主张进一步拓展视野,强调“要‘打通’战前、战后,深入揭示京派及其传统在‘跨越’1949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因为“战后‘京派’的影响通过两部分青年作家得到了延续,都以原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一是当时聚合于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周围,包括穆旦、郑敏、袁可嘉、杜运燮、汪曾祺、盛澄华、王佐良、金隄、周定一等在内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一是当时从国统区出国继续学业的青年作家,他们中后来卓有成就者有鹿桥、程抱一、熊秉明等,其艺术追求明显延续京派影响,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们50—70年代在海外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建’”4。我认为这种叙述强调了京派的文学流脉与文化传承,强调了京派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现实价值,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强调也会扩大甚至模糊对原本意义上的京派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1937年以后的“京派”,已经不完全是当年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地域上的“京派”,也不完全是那个留居帝都的“官的帮闲”的“京派”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符号被固定下来的“京派文化”的代名词了。
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流派中,京派的地域性相对来说是最不明显的,北京对大部分京派作家而言更多地只是一个生存空间与地域空间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京派的创作和存在与北京没有关联。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共同体”5,京派作家形成了与当时的左翼革命文学及海派文学显然不同的文化特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京派作家为什么没有南迁,而选择居留在当时被视为“沙漠”(爱罗先珂语)的北平呢?除了他们所依附的大学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文化取向的选择。20世纪30年代留在北平的作家,无论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还是林徽因、朱光潜,都有自己成熟的独立的文化观,有着一份浓厚的文人学者心态,倾心于安闲、平静的教书写作生活。当时的北平,大到城市小到校园,那种自由、宽松、平和的氛围,正与作家们内心的需要达成了契合。当然,选择留京的作家,还有着一份对北京的深深的喜爱与依恋,北京的风物在作家的笔下哪怕是干燥的气候、风沙、黄昏、冷夜,一派古城的萧索,也很容易引发作家们的怀古幽思,这又与京派倾向于保守的古典主义审美风格不无联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沈从文到了北京才开始回望湘西,南下上海后,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京派特征和属性。同样,在北京时描写湘西,离开北京才越来越感受到北京的吸引力和魅力。这种心态和情形在京派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
本来,京派的地域性是不成问题的,但偏偏被学术界认作是京派的作家绝大多数不是北京人,也不怎么写北京的人和事,再加上学术界也不拿是不是北京人或写不写北京的人和事作为衡量京派的标准,那么问题自然就来了:除了地域性,京派还有什么特征呢?有,这就是超地域性。
京派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结合,超地域性强于地域性则是京派文学的独特之处。超地域性并不显示京派文学本身的削弱,恰恰相反,它反映了京派文学深广的蕴含。作为一种植根于乡土中国的文明理想的代表,今天我们提到“京派”,除了特指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那个特定的文化圈子,以及当年京派作家所共同体现的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学院派气质与文化姿态,还增加了更多的涵义,那就是现代人对自然人性的留恋,对现代都市及工业文明的反讽,对田园牧歌情调的追逐,对清淡、典雅、平和的为文与为人风格的向往。“京派”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精神追求的象征。而这其中纠葛的“京派”与北京的复杂关系,正是“京派”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双重属性的集中体现。
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首先,京派的超地域性是指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京派”越来越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与文学风格的符号被固定和认可。抗战爆发后,大部分京派作家离开北平,散布各地。其中,有一大批京派骨干随北大、清华等大学一起,迁到大后方昆明,包括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卞之琳、冯至、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等,在这个遥远的边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群落,延续着京派的文学理想,并培育了汪曾祺、鹿桥、穆旦、袁可嘉等一大批京派新生力量。虽然时空发生了巨大转换,但这个同时具备了学院与外省特征的作家群落并没有被人们称之为“昆明派”,而是更多地被看做是“京派”的延续,这便更加凸显出京派的超地域性。
第二,从京派作家自身的审美追求来看,其超地域性主要表现在文学审美情趣大于地域色彩上。京派在表现北京文化所体现的某些共同性时,常常超越北京,构成了属于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人们看到了京派文学里面也有“新感觉”,也有心理分析,不光是海派作家有《上海的狐步舞》和《梅雨之夕》,京派也有这种超越传统,超越古典,超越北京地方的东西,如废名的《桃园》与《桥》、萧乾的《梦之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等。
京派除了整体性的超地域性特征之外,作家个人的超地域性特征也很普遍,并更为鲜明突出,从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朱光潜、林徽因、萧乾、师陀到李健吾,他们除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相近的文化格调,在各自的创作中,都具体而强烈地表现出与“京”没有什么干系的个人风格,特别是他们各自的乡土情结和历史文化记忆。周作人曾写过《北京的茶食》,也写过北京的《苦雨》,他那篇著名的《故乡的野菜》也是由北京西单菜市场里出现的家乡的野菜引起兴头的,但是,你看看文章中那股一发不可收的故乡的情思,那种走遍天涯海角也永远割不断的故土的情怀,就可以理解无论怎么称周作人是京派的首领,周作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取向,都是远远超越京派的地域性特征的。
对沈从文来说,的确是没有“京城”就没有“边城”,可是他一旦建构起了自己的湘西世界,你所看到的就绝不止是对理想人性的诗意描写,而且还有对包括“京城”在内的那些所谓文明大都市的理性反思和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沈从文笔下充满野性意味的湘西,就是对古典沉郁的京派世界的超越。说废名是京派作家,除了他与周作人的师承关系,他自己固有的风格与京派文化蕴涵的相通,也是重要因素。但废名那些充满现代主义元素的创作,他的新诗及其诗论,包括《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等小说,都显示了自身强大的个性张力。这种个性张力,不仅使废名在相当程度上与京派作家有很大不同,而且也使他成为整个现代文坛的一个异数。在京派作家当中,另一个典型的异数就是李健吾。
李健吾“与”京派
我在这里用“与”把李健吾和京派连接起来,是想强调李健吾与京派的关系是弹性很大的。
李健吾怎么就是京派作家呢?其一是许多文学史或谈及京派的有关论述,在京派作家队伍的一大串名字后面往往都带有李健吾;其二是有几个材料证明了李健吾与京派的关系:一是几则有关李健吾的小传都有这样一段文字:1933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李健吾在北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从事福楼拜作品的翻译和福楼拜评传的撰写工作,同时参与京派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的编辑,还是新月派后期刊物《学文》的同人6。当然,一些李健吾的小传也都提到了他虽是山西运城人,但10岁起到北京求学,从小即对戏剧和文学有浓厚兴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就与同学蹇先艾、朱大枬等组织文学团体曦社,后又经王统照介绍参加文学研究会7。这些或许证明了李健吾与北京是有相当关系的。但事实上,从1935年起李健吾就到了上海,并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二是尽管李健吾1935年后到了上海,但依然与京派保持着关系。他不仅是1933年朱光潜发起的“读诗会”的成员之一,是沈从文接编后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之一,而且1937年朱光潜、杨振声和沈从文又发起创办的《文学杂志》,李健吾也还是编委会的成员之一8。三是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是京派的一次重要活动,李健吾也是此次评奖活动的裁判委员会成员之一。而《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林徽因编选的小说选,李健吾的作品也赫然名列其中。四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对京派作家的成长、对京派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有着独特的贡献,尤其在《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中,他对沈从文的《边城》、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萧乾的《篱下集》、何其芳的《画梦录》等给予了独到而精当的评析。
众所周知,李健吾的这些批评不仅成为自己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发现”和“奠定”京派作家经典意义的经典之作。以上这些材料表明,李健吾的确参与了京派的一些重要活动,尽管时间不长,但这些活动对李健吾自身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以致他后来到了上海也难以割舍他的京派情结,所以杨义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9。虽然李健吾与京派有着如此明显和密切的关系,但从文学理念到文学风格,李健吾整个的审美追求是独立的、独特的,与京派是合而不同的。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倒不在乎他被谁列入中国现代几大批评家,甚至也并不因为他的文学批评写得如此清丽通脱、质朴明达而自成一体,从本篇文章的角度来说,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似乎更能体现出他与京派的特殊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略作考察:
一是学术界多有把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京派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文学批评加以比较研究,如李健吾与梁宗岱,李健吾与沈从文,李健吾与梁实秋等人文学批评的比较10。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比较论”中,李健吾往往是“主角”,多是把他与别人比,而少见别人之间的比较,如梁宗岱与沈从文或沈从文与梁实秋等。顺便说一下,在有关李健吾的戏剧研究中,也多出现把他与别人相比较的情况,如李健吾与杨绛,李健吾与丁西林等人的比较。这一现象似乎表明李健吾存在着与多人相比较的可能性。的确如此,从文学批评来看,李健吾完全还可以与周作人、废名、朱光潜等人比较。我认为,在这种广泛的比较中,我们既看到他与京派作家的共同趣旨,更看到他不同于京派作家的独到之处。比如感悟、直觉,特别是印象式,是沈从文和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共同特征,然而在这些共同特征中,沈、李二人的差别是很大而且很深刻的。沈从文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和古朴的湘西生活中升发出的人性和诗意,而李健吾则更多地把西方美学和现代主义诗学作用于中国文学的现实性批评;沈从文是把理想现实化,希望他所建构的希腊小庙里供奉的理想人性具有普遍意义,而李健吾则是把现实理想化,李健吾从戏剧、小说到文学批评,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与人的命运,但他关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而是理想的现实,正如他在自己的一篇《关于现实》的文章里所信奉的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最真实的不是历史,而是诗。”11
二是李健吾不仅与沈从文等合而不同,与京派的主要代表周作人也有深刻不同。1936年2月,李健吾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二》当中,提到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的看法:“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正在过渡期,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炼,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字,目下佳作甚少。”12(对周作人的这段话,李健吾注释为:参阅《大公报》本年一月十二日的《文艺》:题目是《中国文学与用语》,长濑诚作,佩弦译。)李健吾对此深表不同,他说:这话得分几层来看。假定站在一个历史的观点,我们便发现几乎所有伟大的诗人,来在一个时期的开端露面。希腊的荷马,拉丁的斐尔吉,意大利的但丁,法兰西的七星诗派,英吉利的莎士比亚,甚至于中国的屈原,绝不因为言语猥杂生硬,作品流于贫窳。言语是表现的第一难关,临到羡赏,却沦为次要的(虽然是必要的)条件。一个灵魂伟大的健全的身体,虽说衣服褴褛,胜过一个多愁多病的衣冠禽兽。所以,站在一个艺术的观点,文字越艺术化(越缺乏生命),因之越形空洞,例如中国文字,临到明清,纯则纯矣,却只产生了些纤巧游戏的颓废笔墨,所谓“发扬性灵”适足以销铄性灵,所谓“光大人性”适足以锉斧人性。我们现时的言语,如若“猥杂而欠调整,乏艺术味”(原文注释为:《中国文学与用语》,长濑诚作,佩弦译),问题不全在言语而更在创造,不全在猥杂而更在调整,至于艺术“味”,天晓得这是怎么一团不可捉摸的神秘,我们只好敬告不敏13。
至此,李健吾尤感不足,接下来又写道:放下“味”,我们不妨拿起艺术。……什么是元朝文学的精华?戏剧。什么是明朝文学的精华?戏剧,小说。什么是清朝文学的精华?小说。这绝不是前人梦想得到的一个评价。这里言语“猥杂生硬”,然而属于艺术。这里呈现的是人性企图解放一个理想的实现。等到一切,甚至于文学,用到不堪再用的时节,富有创造性的豪迈之士,便要寻找一个贴切的崭新的表现,宁可从“猥杂生硬”而丰富的字汇,剔爬各自视为富有未来和生命的工具,来适应各自深厚的天赋。在这时,“猥杂生硬”,唯其富有可能,未经洗练,才有洗练的可能,达到一个艺术家所要求的特殊效果。在这时,你方好说言语创造诗人,虽然骨子里是:言语有待于应用来创造14。
在整个京派文人圈子里,再找不到像李健吾这样对周作人某些看法的绝然反调的了。尤其对周作人用语言的“猥杂生硬”来判断新文学的不成熟,李健吾给予了体无完肤的批驳。其实这不只是对文学成熟与否的某个评判标准的争执,而是对文学本质的某些看法的不同。在李健吾看来,文学是生命的投入与人性的创造,伟大的作家,如福楼拜、普鲁斯蒂,“他们的作品属于高贵的艺术。唯其他们善能支配言语,求到合乎自己性格的伟大的效果,而不是言语支配他们,把人性割解成零星的碎块。这些碎块也许属于钻石,可惜只是碎块”15。
犀利执着的李健吾写到这里,还特地加了一条注释,把自己对周作人的某种不满再次挑明:“就艺术的成就而论,一篇完美的小品文也许胜过一部俗滥的长篇。然而一部完美的长作大制,岂不胜似一篇完美的小品文?不用说,这是两个世界,我们不能用羡赏小品文的心情批评一部长作大制。”16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及文学观告诉我们,同在一个京派文人圈子里,他与周作人、与其他一些京派文人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
此外,李健吾在小说、戏剧、散文和翻译等方面也多有杰作。有人称他是文坛上的多面手和全才,我觉得李健吾的“全才”主要并不是说他创作样式的多面性,而是其风格的多样性和善变性。他的小说既有《终条山的传说》那样的沉郁而又飘逸,篇幅短小而又海阔天空的作品,又有《一个兵和他的老婆》那种类似章回体的传统创制,纯正的晋南方言更是为小说增添了独异的风味。分为上、中、下三卷的《心病》,写了一群精神不健康的男女,他们“没有人过问,冷在旁边永远发霉”。但他们“比比皆是”,“好像夏天一些见不得人的花草,不为人重,漫山遍野长着”。17这是一篇人们提到不多的、很精彩的心理分析小说。
李健吾在文学创作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戏剧。有些学者(如韩石山)在把曹禺与李健吾对比时,一是提到曹禺没有李健吾出名早,二是说曹禺后来虽然名气大了,但其剧作模仿外国戏剧的痕迹很重。言下之意,李与曹虽同样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但李更得中国戏剧之精髓。司马长风也曾这样评价道:“李健吾有一点更绝对超越曹禺,那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而曹禺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可以找出袭取的蛛丝马迹。”18李健吾的戏剧代表作《这不过是春天》是一部经久不衰的杰作,今天读来依然那么有声有色有味道。其实,李健吾的许多剧作包括《这不过是春天》和《十三年》等,都是密切结合现实政治的,不存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吻不吻合的问题。关键在于,不是李健吾对现实生活反映不够深刻,而是我们对李健吾剧作的认识带有很大的局限,包括时代和审美两个方面的。时代局限不用多说,拿审美来说,我们更多地关注李健吾剧作的定位是悲剧还是喜剧。关注对李健吾剧作表现人物“二重性格”和结构上的“三一律”等等,但说到底,究竟什么是李健吾剧作的独特魅力呢?用司马长风的话说,《这不过是春天》“读毕全剧,如听完一曲交响乐,轻妙完美,感到每个音符都有恰如其分的美,而余音袅袅”19。
李健吾剧作的这种完美境地既蕴涵在技巧之中,也体现在技巧之外。有些技巧确是李健吾独有的,比如他在剧本中常常用括号来提示和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一个动作,一个表情,这些括号成了李健吾剧作必不可少的“技巧”:(不见回答;恨恨。)、(停顿。)、(并不恼怒。)、(思考。)、(淡而又淡。)、(动也不动。)、(不耐烦,而又不得不耐烦。)。至于技巧之外,李健吾的剧作更是关乎一个“人”字,人性、人情、人生、人的命运。《这不过是春天》里的革命党人,再革命也难以忘怀旧时的情人,而那位警察厅长夫人,再养尊处优也没有失去人性深处的那些本真的善意的东西。大概这些就是人性超越现实政治、超越漫长时空的动人之处吧。而李健吾把这些处理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实,那么具体,那么看起来实有其事,而想想又似乎没有那件事情也无所谓的,就像这部剧的名字“这不过是春天”,什么意思呢?作者在剧后的“本事”中解释道:“春天去的这样快,眼看夏天就要来了,那时候百花怒发,只有夫人却该萎了。”20多么凄婉的感慨,不为那个革命党人,却为那个厅长夫人!为一个女人的平凡人生!这倒是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太吻合,但不正与人之常情相吻合吗?你革命党人来看我(厅长夫人),我千难万难送走了你,你可以去继续革命了,你有春天了,那我呢?我虽然没有革命,但我不也是很同情和理解你的吗?我的春天在哪里呢?!“这不过是春天”这个剧名有着多么复杂、多么丰富、多么深刻、多么辽远的含义啊!它给人带来的回味、想象与感动,远远没有到今天就完结。
从小说到戏剧可以看出,李健吾是高度个性化的。历史的机缘使他走进京派文人的圈子,而高度的个性,又使他在京派中是个异数。他的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包括深受法国文学影响的个人素质,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使他超越了京派,而这一点又恰恰表明了京派作家本身的一个重要特质:超地域性。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66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