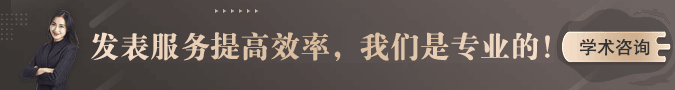戏曲的叙事性探析
本文作者:吴艳萍 单位: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是诗的国度。一直以来,诗歌都是中国正统文化、高雅文学的代表。抒情也无可争议地成为最为主要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古以来,我国的抒情传统如长江黄河源远流长,而叙事艺术却如边鄙小国地位卑微。[1]37
在我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中,叙事艺术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对戏曲叙事艺术的研究就更少了。戏曲虽是从说唱文学发展而来的一种叙事艺术,但以曲为本的艺术样式和长期以来曲是词余、是诗之流别的观念严重影响、妨碍甚至排挤着叙事艺术在戏曲中的运用。但戏曲毕竟不同于诗。戏曲不只是对抒情主人公感情的单纯摹写,还塑造产生这些情感的人物,记叙触发这些感受的事件。随着中国戏曲的演进,传奇的兴起,戏曲更是逐渐向重情节、重叙事的趋向发展。与生俱来的叙事性使戏曲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诗词,戏曲理论家们再也不能对戏曲中逐渐独立的叙事艺术视若无睹。王骥德、吕天成、祁彪佳等戏曲理论家们纷纷在著述中提及或论及戏曲叙事艺术,虽然只是只言片语的零星论述,但却足以说明人们戏曲观念的转变。
李渔在吸收前人戏曲叙事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集腋成裘,将单一零散的理论成果汇集起来,加上自己的艺术经验和独到见解,全面观照戏曲叙事性问题,使戏曲叙事艺术研究的薄弱局面真正得以反拨与促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对戏曲叙事艺术的自觉关注肇始于李渔。李渔认为戏曲是“曲”更是“戏”,是不同于诗文且富有舞台实践品格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叙事性文体。他打通小说与戏剧;强调与重视“宾白”;提出“结构第一”、“立主脑”等主张,确立了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标志着中国戏曲研究开始由重曲、重音律、重词采向重戏、重结构、重宾白的重要转变。同时也促使发端于乐论、诗论的中国曲论摆脱了对传统诗话、词论摹仿的藩篱,推动了中国古典戏曲叙事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成熟。
一、打通小说戏曲———确认戏曲的叙事性
戏曲与小说都是通过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不仅在形式上可以相互转化,在精神内蕴上也表现出相通的特点。兼擅小说、戏曲创作的李渔,认识到二者在叙事上的共通性,不仅在创作上打通戏曲小说,还从理论上确认戏曲的叙事性,得出“无声戏”和“稗官为传奇蓝本”的新颖见解。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小说都是中国古代戏曲素材的主要来源,在中国文学史上,将小说改编为戏曲也已经是一种通例。两种不同文体的改编,最起码在不同的文体之间应有某种可改性。也就是说,小说要有“戏”的因素才能改编为戏曲,成为戏曲之“蓝本”;戏曲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小说相通,才能以小说为“蓝本”。集小说家、戏曲家、戏曲理论家于一身的李渔,不仅深知中国古代戏曲绝大多数源于稗官,且更加深入地了解戏曲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相通———用叙事的方式讲述故事,用对白、动作、肖像描写来塑造人物,用设置悬念、穿针引线、动静结合、发现、突转与巧合等手法来结构情节———这些都足以说明戏曲是与小说相类的叙事艺术。正是这种贯穿于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叙事性,使改编成为可能。素材相承、手法相通的血缘关系使小说无论在“素材”上还是在“手法”上都可以成为戏曲之“蓝本”。正是因为李渔对小说戏曲相同而又相异的叙事技巧和两种文体之间的可改性有着自觉的认识,李渔才会把自己的小说改编为戏曲,才会得出“稗官为传奇蓝本”的独到见解。“稗官为传奇蓝本”不仅体现出李渔对戏曲、小说这两种姊妹艺术之间审美共通性的深刻理解,还传达出李渔对戏曲的定位———戏曲不仅是“曲”也是“戏”,是与传统诗词有着本质区别,与小说具有同等性质的叙事艺术。对戏曲叙事性的确认是李渔戏曲叙事理论的根本与出发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李渔戏曲叙事理论的起点。
如果“稗官为传奇蓝本”的观点指出戏曲与小说异中有同,那么“无声戏”的观点则指出戏剧与小说同中有异。小说与戏曲在情节设计、语言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相通之处,的确有着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所以李渔才会把他的小说合集题名为《无声戏》,在《十二楼•拂云楼》的结尾还写道:“此番相见,定有好戏做出……各洗尊眸,看演这本无声戏。”[2]无声戏的提出无疑是李渔对小说、戏曲同属叙事文体共通性的确认,但李渔对两种叙事艺术的认识并没有止步于此。李渔在确认小说戏曲的共通性的同时也指出小说并不等于戏曲,小说只是无声的戏曲。有声与无声不只是出声与否的区别。有声指戏曲以歌舞演故事,以表演的方式在舞台上完成;无声指小说诉诸于文字,以书本的形式呈现于案头。表演转瞬即逝不容人细细琢磨,书本反复阅读不受时空限制,因而在情节设置上,戏曲往往一目了然,小说则可以表现得错综复杂、曲折离奇……有声与无声的不同是小说戏曲演绎方式的不同,更是叙事特征上的不同。李渔没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也没有逻辑严密的反复证明,他以“无声”两个字极为直接、极为简洁却又十分有效地指出两者的异同,同时也证明李渔对戏曲小说这两种叙事文体有着更为深广的认识。
总之,无论是“无声戏”和“稗官为传奇蓝本”的理论观点,还是李渔改小说为戏曲的创作实践,都起到了打通小说、戏曲,确认戏曲叙事性的功效。
二、提倡“结构第一”———突显戏曲的叙事特征
“结构第一”的主张是李渔戏曲理论夺人耳目之焦点所在,也是李渔对戏曲叙事性特征的突显。
情节结构是叙事性文学的主要构成要素,结构的重要性前人多有言及,“结构第一”的全新观念则旷古未闻。李渔认为结构是戏曲艺术整体的表征,关乎戏曲艺术的生命,是决定戏曲创作成败的关键。故而他一反前人“填词首重音律”的成规而“独先结构”,提出“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3]7把结构置于戏曲诸要素的首位。李渔的“结构第一”是对传统戏曲观念重音律、重词采、轻结构、轻情节的调整与扭转,动摇了戏曲理论的传统格局,体现出戏曲思维方式和审美风范的转移,对戏曲叙事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细绎李渔对结构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关于戏曲结构的论述重心乃至内涵均有变移。《闲情偶寄》的“结构第一”包含了七款内容,其中“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三款与结构布局相关,而“戒讽刺、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四款则属于叙事题材的选择与处理、主题的发掘与提炼的问题。可见“结构”一词在李渔的戏曲理论中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形式,还包括内容,是包括了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艺术构思活动,显示出李渔戏曲结构论较前人的重大差异。
为了更好的安排结构、设置情节,李渔提出了以“一人一事”为核心的“立主脑”。“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它,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对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自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3]19以《西厢记》为例,李渔认为“一部《西厢》,只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正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1]20可见“一人一事”或“主脑”是指对整个戏曲结构起统摄作用的核心关目,是作者萌发创作契机、联络全剧人物的枢纽,是推动戏曲故事向纵深发展的中心事件,也是衍生一系列戏曲故事、成为戏曲肇事之端,而又统系全局使戏曲不至于成为散金碎玉、断线之珠的中心情节与重要的关目。换句话说,李渔明确把戏曲的“主脑“归结为“一人一事”,“立主脑”就是要以“人物事件”为中心,也就是要确立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这显然更符合戏曲与生俱来的叙事特征。
“减头绪”与“立主脑”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头绪主要是指情节因果线和戏曲中的穿插,头绪太多就会使观众应接不暇,也会使作者文思不专顾此失彼难以驾驭。为了突出“主脑”,表现作者“立言之本意”,集中情节形成优化的戏曲结构,就必须减去纷繁的头绪。所以李渔提出要“减头绪”。减头绪“则思路不分,文情专一”[3]30,能使全剧“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3]29“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3]29,从而使情节更集中、故事更单一,从反面保证了“立主脑”的成功。
“减头绪”是从叙事的横向谈情节结构的集中与单一性,“密针线”则从叙事的纵向谈戏曲关目的内部衔接和结构的紧密性。一部戏曲既不能保持生活原始状态的完整性,又要具有艺术的完整性,功夫就在于“针线紧密”。李渔提出:“编戏有如缝衣,其初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3]26可见要让戏曲结构天衣无缝浑然天成,不仅要加强戏曲情节内在的贯穿衔接,还要做好情节间的穿插联络与埋伏照应。只有戏曲结构各部分之间血脉相连,形成有机整体,使主要人物与主要情节得以突出,才能使戏曲作品真正成为一个紧密完整的叙事体。
值得注意的是,李渔主张“一人一事”“一线到底”并不是主张“单线结构”。他提出“减头绪”也并不意味着头绪愈简愈好。他所创作的《笠翁十种曲》大都是复线结构,他的《蜃中楼》更是特意将《柳毅传书》《张羽煮海》合二为一,有意变单线为复线,头绪也更为繁复,都是最好的证明。笔者认为李渔提出“减头绪”“一人一事”“一线到底”,只是主张避免情节线索过于纷繁杂乱,要求在“主脑”的统摄下,处理好主线与副线的关系问题,从而使情节更集中、结构更洗练、故事更单一,更有利于戏曲叙事。
李渔戏曲叙事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表现在他对叙事题材的选择与处理的阐述上。关目“新奇”“非奇不传”是传统戏曲叙事题材选择上的要求,也是李渔一生戏曲创作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将“非奇不传”之“奇”与为奇而奇、荒唐怪异区分开来,为了纠正当时剧坛上流行的“奇幻”之风,李渔提出“戒荒唐”来反对以荒诞不经为新奇的创作风格。他殷殷告诫说:“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无论词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3]32李渔还认为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要想提高戏曲的吸引力、增强情节的生动性,使故事富有新意、关目新颖奇特,真正做到“非奇不传”,不是成天绞尽脑汁去想奇事、写奇事,而是要去发现与挖掘常事之奇、在常中见奇。这就要求选择戏曲叙事题材时要“脱窠臼”,避免因袭前人,勇于创新,以新释奇、以新代奇。正因如此他才说“新即奇之别名”[3]23“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3]24可以说李渔的“脱窠臼”是以新释奇,是对“非奇不传”的传统戏曲叙事理论的深化。
题材的选择与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李渔在提出“戒荒唐、脱窠臼”的同时还提出了“审虚实”。“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幻境之妙,十倍于真”[3]34。李渔清醒地认识到戏曲是区别于诗词文赋、散曲小令的叙事文学,是可以虚构且大多出于虚构的叙事作品。李渔不仅明确承认在戏曲创作中虚构的合理性,还强调不同题材的虚实处理当有所不同。他认为历史题材的创作要“实则实到底”。因为往事“传至于今,则其人其事,观者烂熟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得。”[3]35所以“若用往事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角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3]35但现实题材的写作则可“虚则虚到底”。因为“若纪目前之事,无所考究”[3]35“非其不虑人考,无可考也”[3]35所以“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3]35李渔对戏曲中虚构与想像的明确认可、充分肯定、极力倡导与重视,对不同题材的不同虚实处理,强调题材处理的合理性,都是李渔注重戏曲叙事要素、强调戏曲叙事特征的证明。
总之,李渔以人物事件为中心,强调叙事结构至上的思想主张,突显了戏曲的叙事特征,是对传统戏曲叙事理论的深化,也标志着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理论的成熟。
三、主张宾白叙事———强化戏曲的叙事功能
曲中宾白乃戏曲叙事性的最佳体现方式。拘于传统的偏见,中国戏曲理论从来重曲轻白,即便提及,也只是把宾白当作戏曲创作中无关痛痒的附庸。相对而言王骥德较为重视宾白,他在《曲律•论宾白第三十四》提出“诸戏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难不下于曲”[4]163既揭示出“重曲轻白”的客观事实,又从创作难度上并列曲白。为了扭转戏曲界轻视宾白的倾向,李渔大胆坚定地提出曲白并重的崭新理论,“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
为了突出强调宾白的叙事作用,深知词曲之于戏曲具有生命价值的李渔甚至说了过头话:“至于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3]87“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即是揭示事件之情由,展现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亦即叙事。在李渔之前,人们只是注意到“宾白”的提介人物、插科打诨等方面的作用,而李渔却注意到了“宾白”在揭示事件起因、介绍情节发展等幽隐之处的重要作用。李渔岂有不知曲文传声又传情之理,他的过头话是为了突出强调戏曲宾白的叙事功能。再说做传奇与做文章不同,文章是做给读书人看,传奇则是演给老百姓看。老百姓大多听不懂戏文的曲词,只能当音乐来欣赏,他们要了解剧情人物,确实单靠宾白一着。由此可见,李渔对戏曲宾白的强调,是把宾白作为古典戏曲的叙事要素来强调的,是为了更好的演绎故事、交待剧情,从故事和戏曲的整体叙事性上展开的强调。
在戏曲演出过程中,宾白的叙事功能则显得更为重要。这点在他论及明清传奇的演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传奇一部戏曲往往数十出,叙事结构散漫冗长而又缺乏变化,演绎时间较长,不利于观众欣赏接受。鉴于这种弊病,李渔省略情节、缩长为短。为了弥补省略造成的情节上割裂,他又巧妙地提出用宾白来交代情节线索,使剧情前后连贯又不悖情理。他说:“于所删之下折,另增数语,点出中间一段情节。……或于所删之前一折,预为吸起……如此,则数语可当一则,观者虽未及看,实与看过无异。”[3]114
李渔还通过新旧剧演出时的差别来说明以宾白叙事的重要性:“且作新与演旧有别,《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家弦户诵已久,童叟男妇,皆能备悉情由。即使一句宾白不道,止唱曲文,观众亦能默会。”[3]87所以宾白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且可删可减。“至于新演一剧,其间情事,观者茫然”[3]87,这时就需要用宾白把故事的梗概不时地告诉观众,使观众对故事有个大体的了解,无形之中宾白又起到叙事的作用。
“从来宾白做说话观,随口出之即是,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3]86李渔不仅在理论上注意并强调宾白的叙事功能,还在创作中把宾白及其功能发挥到极致。李渔曾说:“传奇宾白之繁,实自予始。”[3]86朱东润也曾说:“今以笠翁之作考之,宾白之繁实殊于众。”[5]96的确,李渔创作和改写的剧作中,宾白的篇幅都极大,如他改写的《琵琶记•寻夫》和《明珠记•煎茶》两出,宾白要比原作多出一倍。创作的《意中缘•画遇》《比目鱼•改生》等作品宾白之繁更甚,皆前人剧本所未有。李渔甚至连宾白也应前后照应这样的细节也考虑到了,他提醒曲家在创作宾白时应戒绝“前是后非、有呼不应、自相矛盾之病”[3]93,认为只有注意和考虑了宾白的前后照应,曲中宾白才能真正起到使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的叙事作用。在这样大量的前后照应的宾白中,宾白的叙事功能与戏曲的叙事性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李渔对宾白的强调与重视是此前戏曲理论家所没有意识到的,他不守前代规约给予宾白非凡的地位,大大强化宾白的叙事功能,是对宾白艺术的创造性发展,也强化了戏曲的叙事功能,是对戏曲叙事理论的极大开拓。
叙事性是李渔戏曲理论的重心所在,它使《闲情偶寄》较之以往任何一部传统戏曲理论著作更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某些创作问题的实质。李渔以富于体系的理论建树与丰硕的戏曲作品,使传统戏曲叙事理论得以发展,标志着中国古典叙事理论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渔集前人戏曲叙事理论之大成,开创了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理论的新阶段,代表了中国古典叙事理论的最高成就。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61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