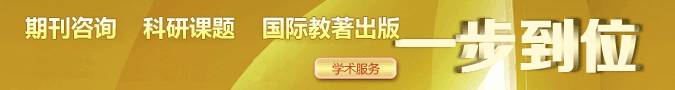戏曲创作中懦弱性格建构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赵婷婷 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
黑格尔说过:“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1]329作为理想艺术的戏曲,同样把性格作为真正的表现中心。戏曲中的人物性格千差万别,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在戏曲故事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懦弱性格作为其中一种,在戏曲文学中同样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一、戏曲人物关系中懦弱者的不可或缺
戏曲要表现人生,就离不开对人物的刻画描写。人物作为戏曲故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既是构建戏曲故事的平台,也是作者表达各种情感的最终载体。然而人的性格多种多样,有强悍者,亦有懦弱者,即便在同一个人的性格中,往往既会有强悍的成分,也会有懦弱的可能,且两者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互相转化。那么,在写矛盾冲突时,经常需要有懦弱者的出现。戏曲文学中懦弱者很普遍,如许宣、蔡伯喈、安秀实、裴少俊、唐明皇、蔡婆、王文举、侯方域等等。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明末东林党人侯方域因遭人陷害,被迫与名妓李香君分离外出逃难。李香君遭人逼婚,但却坚拒力排,绝不屈服,而侯方域最终却变节降清,使李香君失望不已。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中,蔡婆迫于淫威,同意收留张驴儿父子并劝告窦娥嫁给张驴儿,窦娥誓死不从,最终含冤受屈而死。元代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中,王文举面对老夫人的悔婚,逆来顺受;面对倩女的执著追随,他懦弱迂腐;面对老夫人“鬼魅”的一面之词,他拔剑而起,丝毫不顾念三年的夫妻情分。用一句话来概括王文举的形象最恰当不过了,那就是:热衷功名,无情腐儒。清代方成培《雷峰塔》中的许宣更是懦弱者中的典型。他胆小怕事、懦弱被动,一面尽情享受着白娘子的爱和付出,一面又薄情寡义。白娘子何曾有负于他,他却三番五次地亲自带人捉拿白娘子。一旦遇到困难,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然后逃跑。且只要有机会镇压白娘子,许宣都毫不留情,决不手软。懦弱作为一种性格缺陷,在作品中却屡屡出现,是因为懦弱性格在很多戏曲故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作者通过它反映人生、针砭世事、表达情感。离开了懦弱的性格因素,作品的完整性就会受到影响,更谈不上表达主题和情感。
再者,懦弱性格者能更好地衬托戏曲中其他人物的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品质,以便更加鲜明和生动地表现人物。如侯方域的懦弱和背叛,更加鲜明地烘托出李香君的品格和节操,使她的形象更加高大,加强了作者对人物歌颂和赞扬的力度,使得李香君坚贞不渝的形象深入人心。最后,人物性格的懦弱,在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能激发观众和读者的共鸣,使作品更能表现现实,感染观众,让观众在观赏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价值判断,从而与社会价值观相融合,使得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保持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如《窦娥冤》中的蔡婆在让人痛恨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可悲,在蔡婆懦弱性格的推动下,窦娥一步步走向悲剧,悲剧产生的过程比悲剧结果更能激发人的同情悲悯。由此,窦娥的冤屈才得到充分的表现,成为“天下第一冤”。在这个过程中,观赏者同情窦娥、痛恨懦弱的思想被充分调动,与作品形成共鸣。正因如此,《窦娥冤》经过时间的洗礼,至今还在感染着观众和读者。可见,离开了懦弱的性格因素,很多经典剧本无法形成完整的故事;离开了懦弱性格的推动,故事的表现力便会大打折扣。懦弱者在戏曲故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戏曲人物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懦弱性格制约与推动下故事的逻辑发展
戏剧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在戏剧中,对于性格的刻画最有效、最根本的手法就是通过具有直接表现力的故事情节。而情节和性格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故事情节随着人物性格的表现逐步展开;另一方面,人物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变化而体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就推演生发出什么样的故事情节。试想,如果让张飞或者赵云把守华容道,断断不会放走曹操。如果让张飞或赵云有意放走了曹操,就很难使读者信服,因为他们二人缺乏放走曹操的性格依据。懦弱性格对人物关系和故事发展既是制约也是推动。在这种制约力和推动力的双重作用下,戏曲故事可能按照作者设定的逻辑方向发展,并形成特殊的思想表达与审美感染力。
《雷峰塔》中的许宣便是其中典型。剧中许宣原是个生药铺的小伙计,在一次游湖中偶遇白娘子,两人一见钟情。白娘子不嫌弃他出身寒微,家境贫穷,主动提出与其结合。在许宣因家寒不肯应承的情况下,白氏又赠银助其“央媒说合”[2]964。后因赃银事败,许宣虽觉白氏待他“情分不薄”[2]967,但终究“也顾他不得了”[2]967,于是逃往苏州避难。这是故事的第一个波折。接着,许宣又听信法师魏飞霞之言,怀疑白氏为妖精,并接受其所赠灵符以“扫荡妖氛”[2]985。后被白蛇高明化解,许宣则自认“一时昏昧,为彼所惑”[2]987,并保证不会再妄听谗言。这是故事的第二个波折。端阳佳节,许宣再三相劝白蛇共饮雄黄酒,待白蛇现形后被吓死,为救许宣,白蛇舍身盗草。这是故事的第三个波折。而后,许宣因佩戴萧太师府的八宝明珠巾而获罪,再次怀疑白氏为妖孽。为避免再次被骚扰,只好前往镇江。这是故事的第四个波折。许宣到金山寺拈香,听信主持法海之言,认定白蛇为妖,不肯归去。待白蛇寻来,许宣因害怕不肯相见,无奈,白蛇只得与法海斗法,以便救出许宣。在《水斗》中,法海要收服白娘子,但因白蛇“腹中怀孕,不能收取”[2]1017。断桥相会,青儿责怪许宣薄幸,许宣则把责任全推给法海,“都是那妖僧不肯放我下山”[2]1020,“叵耐妖僧忒煞狠,教人怎不心儿惊”。[2]1021这是故事的第五个波折,也是本故事的高潮。待白蛇分娩不久,许宣便暗请法海来驱除白蛇,以免“终为后患”[2]1025。白蛇终被法海镇于雷峰塔下,而许宣也“太觉负心了些”[2]1028,于是出家于净慈寺。故事的结局是金科状元许士麟祭塔喊冤,“感动那古先生”[2]1037,救出白蛇。
至此,许宣的软弱性格展露无遗。相比白娘子,许宣处处被动,处处退却。每次处于困境时,许宣总是首先想到推脱责任,官府只要稍一发威,他便连忙和盘托出,还三番五次地亲自带人捉拿白氏,之后,便逃之夭夭。由于恐惧、害怕,经常怀疑并想办法除掉白氏,全然不顾夫妻情义。作为一个男人,许宣不可谓不懦弱。正是许宣的软弱,制约了情节平坦地向前发展,但同时在每个情节中都推动了故事向前发展。他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制造一个新的事端,制造一个又一个小高潮。如若没有许宣的懦弱性格催生的行动,那么故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进行下去。通过这些生动的情节,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了一个懦弱的性格形象。在这里,事件和性格是融为一体的。正是这样的性格,在这样的境遇里,产生了这样的行为;反过来,透过这样的行为,我们看到了人物生动的血肉丰满的性格。这是情节与性格相互交融的最好例证。再如《墙头马上》中的裴少俊。裴尚书之子裴少俊与李千金一见钟情,李千金勇敢地与裴少俊私奔,并匿居于尚书府的后花园中。裴尚书发现后怒斥李千金,并要“送到官司,依律施行者”[3]48。此时,裴少俊竟说道:“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一妇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写与休书便了,告父亲宽恕!”[3]48虽然故事以喜剧收场,但裴少俊的软弱性格表露无疑。他的妥协,使得一家团圆的结局变得遥远,但同时也把故事推向了一个高潮,使情节与情节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趣味性。
其次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里的唐明皇。唐明皇宠爱杨贵妃,二人相约生生世世为夫妇。但好景不长,安禄山叛乱,唐明皇携杨贵妃仓皇入蜀。驻扎马嵬驿时,陈玄礼请求诛杀魅惑君王的杨贵妃。在叛军的逼迫下,唐明皇对杨贵妃说:“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4]95当杨贵妃哀求他时,他回复道:“寡人怎生是好。”[4]95杨贵妃被叛军带走时,他又说道:“卿,休怨寡人。”[4]95剧中的唐明皇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懦夫形象,几乎不敢进行抵抗。他的懦弱性格决定了杨贵妃命运的悲剧性,最终被赐死也符合故事的逻辑发展,并形成了特殊的感染力。懦弱性格者虽然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不幸,但这样的行为又是符合故事逻辑发展的,使剧情有了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同时还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更能吸引观众。
三、懦弱性格的道德评判与观赏影响
道德涉及的是对人和事的善恶判断。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下,对事物善恶的判断是必不可少的。恰当运用道德因素会使作品具有一种审美张力,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鲜活,提升其艺术美感。对戏曲中懦弱的人物形象,作者往往通过批判其懦弱来表达对人性、对社会的种种理想化追求和想象。未遇白娘子之前,许宣只是个穷酸落魄的小市民,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遇到白娘子之后的许宣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却告别了只身无靠的生活,还拥有了事业和家庭。白娘子不仅仅在物质上拯救着许宣,更给了他真挚深厚的爱和家庭。正当他们可以像童话中说的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际,多疑的许宣又听信了法海的蛊惑,两人安定的生活再次陷入危机。
最终,许宣引狼入室,协助法海收服了白娘子。许宣的这一行为,不仅毁灭了爱情,其家庭也以白娘子被镇雷峰塔、许宣出家、许士麟痛失双亲而分崩离析。将自己和家庭一步步引向毁灭深渊的真正元凶就是许宣自己。多年之后许士麟祭塔时,称“吾父误信谗言,弃家方外,致令母亲身遭镇魇,抱恨重泉”[2]1033(《祭塔》),对双亲的行为作出了公正的评判,毫不犹豫地将感情的天平重重地倾向了白娘子,指责许宣。白氏告诫儿子“但愿你日后夫妻和好,千万不可学你父亲薄幸”[2]1034。通过许士麟与白娘子的口,作者表达了对许宣之类薄幸之人的批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其实是在颂扬白娘子重情重义,不畏强权的品质。
同样是懦弱之人,作者对待蔡伯喈更多的则是同情。《琵琶记》中作者站在封建道德的立场上,写出了一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苦衷,“三不从”而“从”,给予蔡郎以同情。在牛丞相家享荣华之时,蔡伯喈也无时无刻不思念父母和赵五娘,表现了一个孝子义夫的形象。遵循自然人格,他想攀龙附凤,享受荣华;作为社会人他又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良心的谴责。既想尽孝又想尽忠,更不想做一个忘恩负义之人。通过戏剧情节,作者的道德矛头直接指向的是当时封建落后、禁锢自由、扭曲人性的社会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在更高的层次上激发了观众的思考力,从而成功地通过艺术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丑陋面、阴暗面给予重重一击。戏曲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有其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其功能与作用的实现,依赖于对观众的价值引导。“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弗朗西斯库•萨塞在《戏剧美学初探》中说:“不管什么样的戏剧作品,写出来总是为了给聚集成为观众的一些人看的。这就是它的本质。”[5]257
中国明末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非常重视观众,其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观众欣赏。作者在表现笔下人物的同时,又不忘表现他们性格中善的一面。他们虽不完美,却是世俗而真实的人。能够坦诚地道出他们的不完美,不以纯洁神圣苛求他们,正是作者的宽容之处。现实世界中,人的性格作为一个整体本来就具有多重性的特点,不能单纯用好或坏来进行界定,所以观众对戏曲中人物形象的评判更具弹性。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之分,读者就更容易根据自己的经历与喜好产生感情偏向,选择自己所喜爱与支持的那一种人、那一种生活态度、那一种观念,构筑起他们愿意认同的那个主旨。因此,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戏剧中,许宣、蔡伯喈自然不是大善之人,在他们身上流露出许多人性的弱点、缺陷,但他们亦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种种情感,使得人物形象更显真实。如当白娘子被法海收入钵盂时,许宣还是表现出了不忍:“生见蛇,悲介”[2]1027。虽然只有五个字,但也足以勾画出许宣虽想求全自保,却也并非冷酷无情的矛盾而真实的心态。还有人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许宣,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是由那个特定的环境决定的,无可厚非。而蔡伯喈的形象,更是体现出其以孝为先的道德标准,兼有对赵五娘的夫妻情义。所以,从观众的道德评判角度出发,他们的行为还有待商榷。这种可供选择的价值评判和道德判断,使得对戏曲作品的多元化解读成为可能。通过观众多元化的解读,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得到质的提升,从单纯的戏曲作品欣赏上升到价值观选择。在种种价值道德判断的碰撞和融合中,客观上戏曲对社会文化进步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由此,戏曲作品的社会功用得以顺利实现。
然而,戏剧作品在影响观众的审美情绪的同时,观众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对戏剧作品的创作也具有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在不断地演变。剧中许宣的形象由犹豫动摇转向忠贞坚定,法海则变成了破坏自由恋爱的恶势力。在题材发展过程中,人物形象逐渐完美化,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这也是思想上的一种进步。再如早期南戏中的蔡伯喈是一个负心汉形象。蔡伯喈应试上京长期不归,其家贫寒不堪。蔡伯喈父母死后,蔡妻赵贞女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埋葬公婆。当赵贞女到京城找到蔡伯喈时,他却拒不相认,以马踩之,最后蔡遭暴雷轰死。《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不仅不再是原来那个该五雷轰顶的蔡伯喈,反而成了一个该同情的蔡伯喈。这一方面是作者为了宣传儒家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受到中华民族大团圆心态的影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华夏美学追求的理想境界。钱锺书先生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中指出:“这些中国戏曲留给读者的是对更美好事物的向往,而不是对万物有更悲惨的感觉。”[6]观众的这种接受心理也深深地影响了剧作家的创作。综上所述,引导观众形成一定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是戏曲作品实现其社会功用的有效方法,反之,观众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又会对戏曲创作产生影响,戏曲中体现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观众审美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四、结语
人物的懦弱性格,通过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推动观众进行心理上的角色融入来取得良好的艺术表现效果,进而发挥社会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懦弱性格也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中,这样的现实基础,一方面给戏曲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观赏者进行现实融合。懦弱作为一种常见的人性特征,与戏曲创作相结合,诞生了无数经典,在几乎所有的戏曲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出现懦弱者的影子。人性中的懦弱,是人格的多重性复杂性所决定的,戏曲要表达人性,就无法绕开人性中这种固有因素,因此懦弱者的形象将伴随着戏曲创作的发展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57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