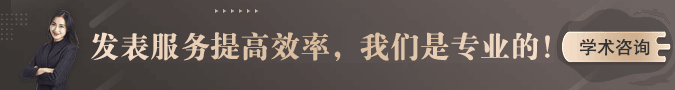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客观性的解构
本文作者:王昆、陈弢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历史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其根本的基石就是历史学自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一直是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依托,以同样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建构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加固。”[1]但是,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文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的“客观中立性”进行了猛烈地解构和挑战。
一、历史学的客观性
沃尔什曾经将历史学的客观性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的而又是最棘手”[2]的问题。王学典在《述往知来》也说道,“历史学中的客观性是个弹性概念,具有量的而不是质的属性”[3]。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沃尔什认为所谓的历史客观性就是“每一个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人都必定会加以接受”[4]的东西。沃尔什对历史客观性的看法是以他对什么是历史事实的认证为基础的。而历史学的客观性概念,实际上借助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客观性的重要条件,乃是人们的普遍同意。”[5]我们永远无法要求历史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客观———从同样的材料或证据出发,按照严格的实验操作或是推理过程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由于历史具有流动性、易逝性和不可重复性,因而历史的客观性则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如果以“人们的普遍同意”为尺度的话,历史学简直没有客观性可言。同时“,历史资料的残缺性、不完善性,历史过程自身的未完成性”[6],也使得历史学的客观性变得扑朔迷离。但历史本身确确实实存在,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及是否能够知道它的存在,所以历史学当然又有自己的客观性制约。历史学中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相比,只有在一种弱化了的次要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
历史学长期以来建立的“客观性”、“求真”的形象,虽然具有真实可信的内核,但从总体上看,其实只是一种在追求客观性的强烈意志支配下的主观愿望,只是一个被夸大了的关于客观性的神话。“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的主观性贯穿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始终”[7],历史学的客观性只能是相对于约束主观性的程度而言。“历史认知活动的媒介、主体和方法的客观性,就决定了历史认知活动的客观性及其程度”[8]。“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客观性即非主观性”,“消除主观性因素是历史认识客观性分析的基本思路”[9]。而要做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在现在看来,是史学家学术良知的一种衡量尺度。同样,我们对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是从不同层面上考虑的,例如“历史事实客观性的要求”、“对历史叙述客观性的要求”、“对历史解释客观性的要求”[10]。但是要做到以上几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史学研究中,我们期待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进而我们在此之上探寻更高层次的主体性。
二、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客观性的质疑
历史学客观性的基本保证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由批判性的检验而确保史料的可靠;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要在研究过程中剔除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而保持严格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都极力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比如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传世之作《历史》中指出,“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但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11]。
19世纪后期,法国史学家古朗治演讲结束之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说道:“请不要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12]可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五花八门、流派纷呈的文化思潮中异军突起,以其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詹金斯曾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运动。而是应时势的需要,贵族的、资产阶级的和左派的理论家们,在诸多领域内所不得不进行的重新评价,其评价的基础根植于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变迁之中。”[13]“从本质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激进主义的典型思维方式,是对现代主义的全面挑战和反叛。”[14]他们抨击历史主义和其关注的重心———人,认为“历史不是以直线形式展现,历史要经历变化无常的危机、混乱、中断”[15]。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作者本人主观构造出来的。它取消了是否存在客观现实以及历史著作是否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现实的问题,而提出历史学家的叙述文本就是现实。当我们只有通过语言的、符号的史料文本去理解、推断历史事件本身的时候,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学者质疑史学客观性的根源所在。而这种质疑又可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的权力支配,揭示其意识形态特征;二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艺术,根据其创作活动的特点,视之为一种语言游戏;三是将历史文本化,贬低作者,抬升读者,从而突出主观解释的意义。”[16]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詹金斯、怀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们都不否认‘过去’的真实性,他们否认的是过去和对过去的叙述之间有任何的联系。认为任何试图揭示‘过去’真相的做法,都没有认识论上的保证”[17]。因为历史学家所要发现的东西,只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动运动的位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18]。
三、后现代主义为史学研究提供新思维
纵观历史学的发展,作为族类记忆和国家记忆的历史在突破了神权限制之后得到了与其他科学一样的学术地位。历史学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时间表,而是在科学的英雄主义引领下向着人性和理性前行的精神火炬。但就以美国历史的编写为例,实质上是存在一个建构历史框架的思维指导,“美国人必须自创,即团结意识,一整套民族象征物、活跃起来的政治热情”[19]。
正是因为这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关注的是精英人物和主导人群,而很少关注普通的社会大众,这让人们误以为历史的编写和推进没有或者很少有客观性。“后现代主义正是这一情景中西方文明内部反思的产物”[20],“以对工业经济时代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全面解构和颠覆为特征”[21]。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更加广泛更加细致,洞悉了历史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关系,学术研究呈现出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生活也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大大提升了读者的地位,促使读者透过文本寻找历史背后的真实,从而突出了主观解释的意义。
其实“后现代主义最为核心和最为有价值的地方,或许不在它颠覆既存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更不在于它是否能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在其批判精神”[22]。但这种批判精神并不能无限的放大,否则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陷入癫狂、无助、虚无的状态。因而在批判的过程中需要掌握一个适当的尺度,例如“坚持史学研究中客观性标准”,“在历史研究中恰当运用史学工作者的主观力量”,“把握好史学客观性和主观性二者的合理度”[23]。那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历史是否有一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24]。在我看来,后现代历史学应该承认的这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是———历史学并不是“任意虚构”。由于人类目前的认知条件和能力,“纯粹客观的历史认知只是一个神话”[25],所以历史学的客观性其实处于一种弹性状态中,它有一个伸缩范围。但是“人类社会有寻求真实、了解真相的愿望,这正是历史学存在的基础”[26]。
从另一角度而言,不论后现代主义怎样去摧毁现代史学的客观性基础,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个真实客观的标准立于其背后。“后现代主义没有给历史研究提供成体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对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应当积极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原因所在。”[27]最后它给我们提供了大写历史背景之下的小写历史的新思维。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49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