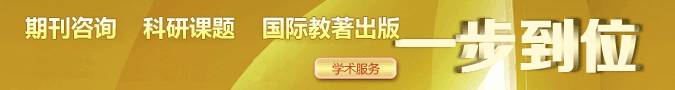塔里木盆地环境历史变迁
110ka来环境变化的沉积记录
近年来我们在南疆多处采集了不同地质剖面的样品,并根据文献[1,2]提出的孢粉A/C(Artemisia/Chenopodiaceae)值、地化元素综合干湿指标以及有机14C的样品测定后,再以最小二乘法计算出剖面的平均沉积速率,以此对剖面进行年代插值,其结果与14C数据相互验证,分析了地球化学元素、孢粉、碳酸盐稳定同位素含量的变化[3~5]。现以南疆博斯腾湖沉积剖面分析的综合结果(图1),结合其它剖面成果,将10ka以来南疆自然环境变化分出以下6个阶段:11.0~10.0kaBP,此期中δ18O、δ13O以及CaCO3降至全剖面的最低值,代表了一次强烈的降温事件。此时δ13C降低可能与湖面冰冻时间增加,导致湖水与大气CO2同位素交换程度的降低有关。它很可能是末次冰消期“新仙女木事件”的反映。此时地层中发育碳化层,而A/C峰值的出现及与前期明显增高的孢粉浓度和C值,暗示了相对湿度的增加或者降水与蒸发状况的改变,有利于荒漠植被发育。l0.0~9.0kaBP,δ18O、δ13O以及CaCO3平均值显著增高,气候总体特征较前显著变暖。在9.4kaBP,δ18O及δ13O分别增至全剖面的最高值和次高值,而A/C值与C值却大幅下降,孢粉浓度最低只有8粒/g。这是一次暖干期。自9.0kaBP开始,δ18O、δ13O值降低,至8.8kaBP前后达到一谷值反映了气候由暖转冷的突变性特征。此时,A/C值和C值有小幅上升,地层中发育碳化层(8260±300aBP),代表了相对冷湿的环境特征。8.0~7.0kaBP,本期中δ18O、δ13O以及CaCO3又同步上升,在7.5~7.0kaBP到达峰值。而A/C与C值却在低值水平波动,孢粉浓度只有8~25粒/g。表现为暖干事件。在7.0~6.0kaBP之间,δ18O、δ13O两者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δ13O降低的幅度明显小于δ18O,很可能是全新世大暖期的反映。此时温度上升,空气湿度增大,相应地,A/C值与C值从7.0kaBP前后开始增加,至6.0kaBP左右到达最高值,孢粉浓度此时也升高至215粒/g。这是全剖面唯一的最为显著的暖湿期(气候最适宜期)。其它研究也表明此时为一显著的暖湿期[6]。5.0kaBP之后,δ13O出现一小峰值,而δ18O以及CaCO3含量却呈现下降趋势,反映气候转冷。后期A/C值及C值明显升高,孢粉浓度增至100粒/g,地层中发育炭化层,有利于荒漠植被的生长。在普鲁剖面为一生草层[7]。
4.0~3.0kaBP,δ18O、δ13O以及CaCO3皆呈现高值,孢粉平均浓度A/C值和C值下降。体现了暖干的环境特征。在距今3.0~2.0kaBP,δ18O、δ13O以及CaCO3同步降低,而C及A/C值却有所增加,孢粉浓度增至66粒/g,沉积剖面中出现较厚的炭化层。在策勒县达玛沟剖面中发育粘土沉积[4]。表明这一时期相对的冷湿。在欧洲称之为“新冰期”。距今2.0~1.5kaBP,气候再次转干,达玛沟剖面出现河流相的细沙与薄层的亚粘土互层的沉积[4]。在1.5kaBP前后,δ18O、δ13O降至全剖面的第三低值(图1),虽然CaCO3、C及A/C值变化不明显,但孢粉浓度猛增至135粒/g,反映存在着一个短暂的冷湿期。在1.0kaBP左右,再次趋于暖干,δ18O、δ13O以及CaCO3同步呈现小峰值,而A/C值平均仅为0.2,孢粉浓度只有1~8粒/g。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达玛沟剖面中在这时首次出现风成的灰黄色细沙,并且自960±70aBP后,剖面沉积完全为现代风沙[4]。
近800年来,塔里木盆地南缘气候总趋势是继续变干。但在约630±80aBP后为一湿润期,这一点在策勒县塔格勒剖面孢粉及沉积地层学资料中反映的很清楚[5]。此后,在200aBP前后又有一个短暂的湿润期,地层中发育了滞水环境的泥炭层(仅5cm)。之后剖面中主要沉积的是风成沙。表明此地区的干旱化进一步加剧。塔里木盆地南缘环境演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青藏高原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已大面积的抬升到3000m,特别是中更新世末期以来隆起至4000m,使得输送高度在3500m的来自印度洋的湿润西南季风不能进入新疆,同时东南季风也难以到达,塔里木盆地出现了第四纪沙漠。这是塔里木盆地环境演变的大背景。二是晚更新世晚期以来新疆地区气候演变的模式有别于东部季风区。除全新世大暖期中两者同步外,其演变模式是暖与干、冷与湿的配置,而不是暖湿、冷干。换言之,在新疆寒冷期相对湿润,温暖期相对干燥。这是其气候演变的特殊模式。三是气候虽然有过多次的波动,但冷湿期愈来愈短,暖干期愈来愈长。气候变化的总趋势是不断变干[3]。
2社会兴衰的历史记录
据我们的调查、历史记录以及文物古迹的分布情况[8~10]①,现以塔里木盆地南缘部分流域为例(表1),可将此地区社会兴衰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6500~10000aBP前,塔里木盆地南缘已出现人类活动。目前所发现的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山前地带的河流阶地上,证明山前的草原地带是早期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①。例如:尼雅河上游的纳格日哈、乌鲁克萨依以及克里雅河上游的康苏巴什勒克处石器遗址(表1)。那时的古和田人利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进行着简单的生产劳动。4000~3000aBP前后,各原始聚落相继进入青铜器时代①。金属工具的使用,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人类有更强大的力量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活动空间更为扩大,交往更加频繁,并开始顺河而下,在适宜种植的河流下游地区采集、狩猎、生殖繁衍,建立了沙漠中的绿洲城国,形成绿洲文明的发展。公元前3世纪左右,塔里木盆地南缘现今沙漠的中心地带已建成数十个城邦,较大的有于阗、精绝、戎卢、弥、渠勒、皮山[11]。从出土的文物可以肯定,这时已是畜牧业和灌溉农业并重发展的生产经济。精致的木器、陶器、毛纺织品等反映了手工业也很发达。
公元前2世纪,在张骞通西域以后,西汉王朝开始经营西域。汉朝在乌垒(今轮台策大雅)设西域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管辖西域各地军政事务。汉朝统一西域后,密切了内地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引入了中原地区耕作、灌溉和金属冶炼技术,并且社会相对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生产迅速发展。农业已相当发达,修渠筑坝,引水灌溉,种植了多种水果、蔬菜、粮食作物[11]。至公元3~4世纪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已成为当时塔里木盆地4个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公元3~6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烽烟不断,长期分裂,对西域的管理和统治削弱。各种政治势力在此地区争雄,但都没能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局面。虽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但战乱频繁,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环境,很多邦国在此时被废弃。如:喀拉敦(表1)、楼兰、海头、精绝、阿孜吾加木、克孜勒塔木等[9,10]。公元7世纪中叶,唐王朝统一了西域。社会安定,生产飞速发展。在经济的带动下种植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佛教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进一步繁荣。这是塔里木盆地南缘文明辉煌灿烂时期。大批邦国和佛教寺院在这一时期兴旺发展。
公元9~10世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衰落,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西域也再一次陷入分裂割据。先是吐蕃政权乘虚而入。其后,喀拉汗王朝征服于阗,对此地区进行统治。战乱纷争,不少古绿洲消失。如:丹丹乌里克、乌曾塔提、铁提克日木、哈得里克等遗址(表1)。13~17世纪,元明时代。战乱频繁,政局不稳,经济文化受到破坏。如:卡拉沁古城(表1),特英木古城,德日瓦孜里克古城等都被废弃[10]。
3人地关系变迁的耦合过程
结合塔里木盆地南缘人文与自然变迁的记录,此地区人地相互影响的演化过程如表2。6.0~10kaBP气候有几次冷湿、暖干变化的交替。处于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主要居住在河流出山口的洪积台地上,在山前草原带以狩猎、采集野果为生,利用大自然的成果。4.0~6.0kaBP即冰后期的气候最适宜期,这时的孢粉平均浓度是10ka以来最高的(图1),表明自然环境特别适宜动植物的繁衍。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也是以暖湿为特征,反映了全球宏观背景条件下区域的一致性特征。自然界为生物和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这时随着生产工具的进化(青铜时代),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大大加强,沿河而下,进入各河流的中下游地带(塔克拉玛干沙漠)垦荒、猎狩,生存空间扩大。如果没有气候最适宜期这一大自然环境背景,只掌握简单生产工具的人类很难在已经沙漠化的塔里木盆地中心生存。2.5~4.0kaBP即全新世中晚期,随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活动范围迅速扩大,虽然气候不断的变干,但3kaBP年左右的“新冰期”引起的气温下降,气候较为湿润。骡、马的使用,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有更强大的力量改造大自然,并能面对较为严酷的自然环境。畜牧业、农业生产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有十分简单的社会管理机构。
公元前3~6世纪,这时已不同于早期,气候的干旱使得水量减少。从《禹贡》和《山海经》等书中可知,此地区北部在2000多年前就有流沙[12]。但前期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形成众多的邦国。同时人类能够在此生存,生产工具的飞跃发展也是重要的因素。生活在河流周围的人还是充分发展自己的畜牧业和灌溉农业。后期战乱不断,在政治、军事的角逐中,经济、文化生产发展缓慢,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很多邦国受到破坏,留下片片残破的废墟。公元7~9世纪,气候上为一个短暂的冷湿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后最为兴盛的唐王朝时期。经济繁荣、事业昌盛、社会稳定,在很多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灌溉用的渠道。人类的经济和社会交往更为频繁。从目前所获得的资料看,很多古遗址群的规模都相当大(表3)。反映出当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都比较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
公元10~12世纪,干旱达到小高峰。在策勒县的达玛沟山前河流剖面中,河道已全部被风沙填埋。风沙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同时战争不断,社会不稳,民不聊生,出现割据局面,多种势力在本地区有过尖锐、剧烈的冲突,很多邦国消失。公元13~19世纪,虽然有几次小的气候湿润期,但总趋势是气候更进一步变干,水源补给不足,沙漠扩大。同时生产工具的发展,使人类有了更为强大的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他们砍伐森林,垦殖土地,引水灌溉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策勒县附近的老达玛沟遗址在19世纪废弃(表1)。1997年我们在该地考察时,仍能见到沙地上随处散落着红色的陶片。但黄文弼先生在其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所述的“西南东北一线,绵延约数里,房屋虽已毁败,但审其痕迹,街衢巷陌尚可辩识,中有大道一条通向东北,显然为一旧城镇之残迹……”[15]等景观已大部分被沙漠所掩埋,很难辨认。早期建筑所用的木料已被当地居民做为燃料拉走。
4结语
近万年来塔里木盆地南缘虽曾有过不同的民族、部落、邦国以及冷暖、干湿交替的气候,其生态环境演化、人文历史变迁基本上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若两者都处于“适宜期”(即气候湿润,水量丰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和睦),则有利于绿洲经济、文化、生产的迅速提高发展。例如,汉、唐时期。反之,则环境恶化,沙漠化过程加快,绿洲废弃。如,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在其历史变迁中,早期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所占比重大,而后期人文力量起主导作用。这是该地区自然与人文耦合关系变化的总规律。
自然条件决定了环境的特征及其演化的内在基础。没有降水丰富、植物茂盛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古和田人从山前的草原带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是不可能的。水是干旱区绿洲赖以生存的基础,水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各绿洲的繁荣与消失。而气候的变化控制着水量大小。水量周期性的波动特性决定了绿洲系统的可变性和脆弱性。诚然战争等人文因素可以使绿洲消失,但不会仅使其向河流上游迁移。人类不断向上游迁移这一大趋势,是以自然环境的影响为主。塔里木盆地南缘人类居所在空间上的主要迁移路线是:早期,河流中上游的山前地带(山前草原带);中期,河流下游(沙漠中心);晚期,河流中游(沙漠边缘)。这一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可能正是气候的变化。除水量的变化外,河流改道也是影响绿洲变迁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若水量不变,而仅仅是河流改道,古绿洲大多不是沿河流上、下变迁,而是在河道的左右变动,因为主导变化的因素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对自然的变化有一个短暂的适应期,即自然变化在前,人类社会变化在后。因此,一般情况下两者不完全同步。绿洲的变迁主要发生在河流地带。由于早期的大环境已是沙漠化,河间地带的沙漠始终在不断缓慢扩展,因此,自汉代以来沙漠向南移动了80~100km距离的认识显然不太符合实情。气候逐渐变干的大趋势造成持续的沙漠扩张。但某些局部地区则显示着其特殊性。
如:民丰县安迪尔河流域,古绿洲的多次变迁主要是在现今的安迪尔牧场附近,并没有大幅度的向南迁移。其废弃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社会人文因素。在干旱地区毁林开荒,屯田灌溉,一方面引起沙漠化,另一方面因不合理的灌溉将产生土地的盐渍化。目前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很多古绿洲土壤盐渍化严重。这可能也是古城被废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自然与人文这对关系中,自然环境是缓慢变化的,人类活动却是最活跃、最能动有时甚至是决定自然环境变化过程、特点、类型的主要因素(如:战争、砍伐森林、不合理的引水灌溉,引起河流下游地区沙漠化等)。这在自然生态环境特别脆弱的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特别是随着劳动工具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加强,自然环境变化日趋迅速。早期仅有石器的原始部落在山前的草原带生活了几千年,而后期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使自然环境变化的速率大大加快。仅仅几百年就会出现一个变化的周期。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逐步增大的。在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人类力量对环境影响很小。随着青铜器、铁器以及农业的出现,大规模的引水屯田,砍伐森林,人类不断向自然索取。当超出自然的承受力时,将导致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活动是在客观的、内在的自然条件基础上,作用于生态环境。在自然地理条件十分严酷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塔里木盆地南缘,人类活动更易引起邦国的兴衰,生态环境的恶化,生存空间的转换。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37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