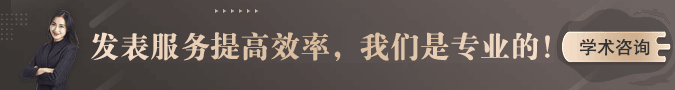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鬼之声>序》(1907年),《<行乐图>后记》(1912年),《<碧芙蓉>后记》(1912年),《<明月亭>后记》(1912年),《<江上月>后记》(1913年),《<云外运>后记》(1914年),《<金刚门>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20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