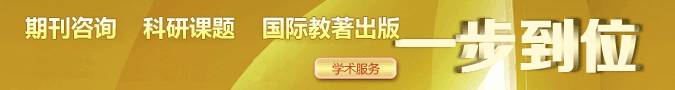比较文学人类学研究
1以人类学视角研究比较文学的意义
自人类学诞生的初始阶段,人类学家就将神话、诗歌、传说等文学形式纳入到人类文化的范畴进行研究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不同族群的文化、文学现象,人类学当中的跨文化的文学比较成了人类学和文学的交汇点。起初,以人类学研究比较文化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学科定位和位置,被相关学者认为是旁门左道,并不入流。而在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文学人类学的关注,使其成为了一个既前沿又略显边缘化的学科。前沿化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在神话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的文化人类学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并在世界文学人类学界位居前列。但是其边缘化的问题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这门学科一开始在学科归属上并不为传统的学科所接纳,之后才在比较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渐渐壮大。我个人认为,以人类学来研究比较文学,也应当是在进行一场比较文化的研究,它给文学的创作和意义带来了不同的声音,它将透过文学创作的文本文字、艺术形式、审美价值以及它的社会意义,来发掘其根本的深层文化涵义和内因。并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内因,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2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学作品《SonsandLovers》、《孔雀东南飞》以及《金锁记》的比较
2.1《SonsandLovers》以及《金锁记》里女主角人格异化的精神分析
《SonsandLovers》和《金锁记》是在中英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在其文中我们可以找到“性格”相似的女主人公。我所说的这种“性格”并非是女主人公莫瑞尔太太和曹七巧天生从娘胎中带出来的生物意义上的遗传基因所致。而是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后天“性格”。是其人格异化的产物。无论是《儿子与情人》中的莫瑞尔太太,还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们所面临的共同的无法摆脱的问题就是婚后妇女从属于丈夫的社会属性的地位以及无法改变自己婚姻状态的苦衷。面对自己爱情的缺失和强烈的诉求,她们都选择了将爱继续放在了狭小生活范围中唯一的异性———儿子的身上。在这种女性处在从属地位、无法真正追求自己婚姻爱情幸福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导致了两位女主人公人格异化的悲剧产生。
2.2人格异化的产生原因及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格有两个基本的规定:其一,人格标志着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点;其二,人格标志着人的个性特征。因此,人格既是社会环境制约的产物,又是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人格(Personality)有时也译为个性,从词源上来说来自于拉丁文“Persona”,指的是希腊罗马时代喜剧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人格在心理学范畴通常指的是一个人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心理面貌。人格对人的社会行为也有制约的作用,它不但可以成为社会行为的内在动力来源,而且可以影响到行为的意义、行为的方式和行为的结果。在后来的精神分析家尤其是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对自我和人格的研究影响到了文化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卡丁纳进一步探讨了文化与人格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为了表征文化,卡丁纳还提出了“制度“的概念,分为初级制度和次级制度。他还提出了“基本人格结构”,在他看来,基本人格结构是同一种文化背景中的每个人都具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性格则是同一制度或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独有的特征。基本人格结构是由初级制度塑造的,转而又投射为次级制度。前者体现了文化对人格的制约,后者则体现了人格对文化的影响。[1]
2.3《SonsandLovers》以及《金锁记》里的“俄狄浦斯情节”
作品中,面对怀有同样畸恋的母亲,两位儿子都有着略微相似的气质,他们身上都有着无法摆脱的“俄狄浦斯情节”。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佛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性发展的对象选择时期,开始向外界寻求性对象。[2]对于幼儿,这个对象首先是双亲,男孩以母亲为选择对象而女孩则常以父亲为选择对象。小孩作出如此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性本能”,同时也是由于双亲的刺激加强了这种倾向,也即是由于母亲偏爱儿子和父亲偏爱女儿促成的。两位女主人公对儿子的“爱护”有加,使得两个儿子内心深处的“恋母情结”,也即“俄狄浦斯情节”被触发。致使他们始终活在母亲“爱”的阴影下,无法真正追寻自己的爱情,他们从内心深处同情母亲的遭遇,变成母亲最忠实的守护者。面对自己的爱人的懦弱和面对着母亲的顺从、不敢反抗以及这种无所适从的感情状态就不难理解了。
3《孔雀东南飞》以及《金锁记》里影响婆媳关系的人物性格因素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叙事长诗。它讲述的是汉末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刘兰芝一见钟情,天赐姻缘,但令人扼腕的是,焦母始终不能接受儿媳,婆媳矛盾重重升级。刘兰芝婚后二、三年就被专横粗暴的焦母休回娘家,她发誓不再嫁给他人,一心等待焦仲卿再来迎娶。然而太守相逼其改嫁于其子最终将她逼向绝路,和焦仲卿约定共赴黄泉。兰芝再婚之日,投水而死,而焦仲卿闻讯也自缢于庭树,留下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情悲歌。《孔雀东南飞》中,对刘兰芝的描述是,“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当。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可见其称得上是端庄淑女。而“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也可知兰芝不但在外貌上无可挑剔,才能也超过了同辈的贤德。这样一个在世人看来算得上是“好儿媳”的女子,怎么会遭到婆婆的厌恶,以至驱赶呢?原因可大致归纳为两点:一是,兰芝不懂得婆婆“粗暴”背后的心理机制。二是,兰芝无意间犯了封建伦理“七休”中的“无子去”。首先,兰芝的婆婆焦母,年轻为人妇时,严格要求自己,尽善尽美地伺候公婆,侍奉夫君和幼子,基本无可挑剔。丈夫死后,常年守寡在家,更是将全部的生活重心与希望托付给了儿子,始终也盼着儿子能晋官加爵,而一心指望的儿子此刻却完全陷入了与兰芝的新婚燕尔之中,焦母显然有种被儿子忽视、抛弃之感,这也是一个早早被丈夫抛下的寡妇最为悲哀与担忧之处。她生命中两个所爱的男人终究还是要离开她。
而她即刻将这种不满与愤怒归结给了兰芝,给她繁重的织布任务来变相惩罚她夺取自己爱子的苦楚。少言寡语、不善阿谀婆婆的兰芝,却是外柔内刚的性格,长期的受压导致终有一天站出来公然与婆婆对抗,以至发展到最后被婆婆休回娘家。而我所强调的第二点,则是要回到汉代《大戴礼记•七出》说:“妇有七去:无子去,淫去,不事舅姑(公婆)去,口舌去,盗窃去,妒忌去,恶疾去。”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了其中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地休弃。兰芝嫁入焦家二、三年,婚后无果,按照当时的封建礼数,这确实也是说不过去的。无法给家族延续香火、让门庭兴旺的媳妇,在封建礼教牢植于心的婆婆心中又怎能称心如意呢。而长期受母亲管制、控制的儿子焦仲卿,在母亲执意要休去其妻兰芝时,也只好无奈,顺从母意,休妻暂做缓兵之策。直到最后也无法与母亲对抗,只好以死抗争。《金锁记》里的麻油店出身的七巧嫁给大户人家姜家患有软骨病的二少爷成为二太太,是以其青春健康、可为姜家生儿育女为代价的。“婚姻是个骗局,等同于被父兄充当买卖的媒介”[3],于是她怨恨“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4]在这无爱的婚姻中,七巧将爱转向了自己的爱子。她用一生的幸福与艰辛努力所换来的一切最终不过是为了儿子长白—“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一句话揭示了七巧一生在精神上依赖儿子,终身甘心情愿为儿子奴隶的心态。甚至急欲控制儿子的感情,精神上完全占有儿子,她让新婚的长白接连三个通宵陪着自己抽烟,诱导他说出媳妇的种种不是,并最终将儿媳逼迫致死。“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5]两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恶毒”的婆婆,无论怎样极尽其“恶”,但终是女人,总都是从媳妇一步步走到了婆婆的位置。她们对待儿媳的种种处置,是在父权制、男性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社会环境中慢慢演化而来的。长期的不幸婚姻生活和受压抑的人性,使得她们无从善待自己的媳妇,总与其争夺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儿子的爱恋。最终导致了两个女人、两代人、代代循环的厄运。这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对女性不公的结果使然。
4结语
无论是西方的《SonsandLovers》,还是东方的《孔雀东南飞》和《金锁记》,透过其凄婉的悲剧文学的表达形式,透露给我们的绝非简单的艺术价值和华美的文学功底。它们在偶然之中,必然地达成了共识,向人们揭示出父权社会下女性生活的不易、以及这种强权对女性的不公待遇,以及人性异化的摧残。也诵过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其文化的共通涵义,那就是,女性,永远只有与男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之上,才可以活得自如,社会才不会陷入无良的纠葛之中。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18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