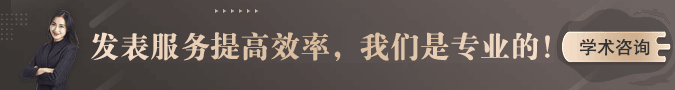文化研究理论创新启发
一兴起与传播:大众文化与“美国化”威胁
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二战前后,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诸多力量的推动下,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大众消费社会的国家[2]P54并实现了文化转型,大众文化逐渐顶替了“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文化成为主流。这种文化以广大的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级为主体,包容了一切与消费主义相关的生活要素,如通俗艺术、体育赛事等[3]P40-48,简而言之,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大众文化即是美国生活方式。随着美国经济、政治、军事的扩张,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被输往世界各地,尤其是英、法、德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成了大众文化输出的最大场所。反映了“美国梦”的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等很快就占据了这些国家年轻人的心,它们成了美国传播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世界观、价值观的载体,悄悄地引导着西欧国家走“美国化”(Americanism)的道路。[4]P157-163与美国相比,当时的西欧国家还未进入消费社会,等级分层比较明显,因而“大众”一词主要指的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普通百姓。另外,西欧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文化”在西欧社会主要指高雅的文学艺术和贵族气派的生活方式,是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获得的少数人的资源。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大众文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出于对作为“他者”的美国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对自身文化特权的维护和对本国前途的担忧,西欧的精英阶层对这种缺乏高度与深度,没有历史意识和崇高品质的文化形态[5]P57进行了曲解式的讽刺和挖苦,企图引导大众自觉抵御“美国化”的进程[6]P5-11。相比而言,西欧广大人民则对给予他们愉悦和享受的大众文化产品并不排斥而且愿意掏腰包,这与精英阶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英与大众,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在大众文化问题上的对立性,使得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在西欧理论界那里被问题化(problematic),这样就把一个新的理论空间推到了这些知识分子面前,这正是严肃的大众文化研究发端于西欧而不是美国的原因。
二亲知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
与大众文化的总体性话语讽刺的是,“推动”这项理论工作进一步发展的不是某个学科带头人,而是希特勒[7]P408。20世纪30年代,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迁往美国[8]P271,此后其成员纷纷进入到美国的媒体或政府部门,亲眼目睹了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9]P24,因此对大众文化有了更多设身处地的直观与亲知,其观点的深入程度远远超过走马观花的文化旅行者,对西欧的“消极美国观”也具有纠偏作用。[5]P541949年社会研究所迁回德国,这群学者发现,战后西德就像当年他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8]P276,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事情,批判资本主义,需要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因此,严肃的大众文化研究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开启的,而这项工作的第一本代表作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在书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考察了被纳入到工业体系中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凭借强大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传播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了大量廉价的文化产品以供选择,表面上使得消费者有足够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商品和娱乐方式。实质上,消费者在文化工业的宰制力量下并无质的自由而仅有量的自由:可以选择商品A或者商品B,却无法选择拒绝文化产品,否则便成为文化中的“他者”或者大众中的异己分子。铺天盖地的文化工业体系扼杀了大众的批判能力和否定性思维,造成了虚假的同一性和标准化的个性,最终还攻占了艺术这片自留地,导致了高雅艺术的边缘化及其救赎功能的丧失,其后果就是将自由主义的社会推到了极权主义的深渊,把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捧为英雄。[10]P107-152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待美国大众文化和它的潜在形式——德国大众文化是带着三副有色眼镜的,一是阶级的,二是国家的,三是种族的,因此他们看待大众文化的模式也刻下了时代的烙印,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文化工业生产的参与者,对文化产品的制作和推销过程那些不为人所知的阴暗面有所亲知,因而对蒙在鼓里的大众深感同情。另外,由于他们受过高雅文化的熏陶,对下里巴人东西的偏见阻碍了他们对这些产品做进一步的了解,更不愿意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对产品进行细读,因此他们并没有深入到消费者与文化产品的真实关系中,所得出的结论,想象和逻辑推衍的成分较多[9]P15-16,实证研究较少。其次,在德国,文化主要指的是精神创造物,如经典的文学和艺术,而在美国,文化不仅包括前者,也包括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加上前面的原因,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限定在艺术化的文化世界里,较少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众生活方式。再次,上述原因还导致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将消费者看成文化工业的顺从被动的客体,而不是多样化的主体,所以他们看到的是极权主义的大众文化而不是民主的大众文化,因而过多地强调了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大众文化和希特勒统治下的法西斯文化的一致性。[12]P9最后,前两副眼镜加上特定时代的犹太人身份,又让他们看问题的时候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和愤世嫉俗色彩。作为左派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历史创造者”——普罗大众的蔑视,也引起了后来人的不满。[9]P38可以说,在三副眼镜的视野下,文化工业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定了基调——大众文化的否定性话语。在英国学者的刻板印象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始终是精英主义的代名词。不过,毕竟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通过“俯下身来”与大众文化面对面地打交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欧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的看法,在将大众文化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同时,让世人认识到大众文化的重要性,提醒世人:文化非小事,它亦可成就人类,亦可毁灭世界,因此,大众文化研究是严肃的,必要的,它需要被提升到社会总体性的高度进行批判,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总体性话语,也为西方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做了铺垫。同时,他们在肯定大众文化的重要性和全盘否定大众文化的合法性之间留下了一个解构空间:既然大众文化如此具有危害性,人民却如此喜欢,而批判大众文化是为了解放人民,那么从一种现实主义的角度考虑,我们就不能“单向度地”考察大众文化(仅仅作为意识形态),而是应该将之置于大众参与的总体社会关系中,把大众作为文化主体来看待。
三怀旧与介入:利维斯主义与作为文化主体的人
与德法相比,英国与美国文化上是同源的,因而英国的文化反美主义并不典型,因而在文化工业理论盛行的40-50年代,英国并没有类似的总体性理论出现。不过,当时英国的文学批评扮演了类似的作用,它是英国人文学科的中心;众多的文学批评作品,建构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总体性景观[14]P112。当时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F•R•利维斯创办了杂志《细察》(1932-1953)季刊,形成了《细察》集团以及利维斯主义学派,统治英国文学批评近40年之久。[15]P10-13所谓利维斯主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指一种方法论的取向:利维斯反对在文学批评界中理论先行,阅读在后,给文学文本贴各种“主义”标签的“哲学化”倾向[16]P50-51[17]P12,主张对文学文本进行近距离地细读、分析和感悟[18]P10-11。这种细读不是封闭式的,而是以文本为跳板,以道德为标准对社会进行批评。因此,文学批评家是带着比一般人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怀介入到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他们需要远离大众以保持独立,才能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方法论取向的利维斯主义也必然导致了另一层意义上的利维斯主义,即理论取向的利维斯主义,这典型地体现在利维斯于1930年发表的小册子《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上。一般而言,“文明”(civilisation)与“文化”(culture)二词在英、法、德三种语言那里基本是可以混用的。[19]P137-140不过,利维斯并没有采用这样的语义而是跟随马修•阿诺德[20]P12,赋予了“文明”与“文化”特殊的对立含义[21]P26:文明指工业化社会的总体形态,其基本特点是商业化和大众消费主义,以美国社会为典型[22]P16;而文化则由精通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少数人所掌握,它以拥有“伟大的传统”的英国文学为典范,理应规范着文明的走向,不过在20、30年代,英国正在步美国的后尘,少数人已经被波涛汹涌的大众文明围在了墙角[21]P3-12,社会已经处在了堕落的边缘。利维斯深知:“对抗机器的胜利终究是徒劳的”[21]P31,但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发动少数人夺回逝去的权力。由于这样一种文化情结,利维斯否认了“大众文化”[21]P20的合法性,展现了他的欧洲精英论的成见。这似乎给人以一种印象,即利维斯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是殊途同归的:一、当时他们已经认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的关键作用,共同开创了大众文化批判这个领域;二、他们有着共同的精英主义情结,因而后人将这两个学派并称为“文化精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没错,但共同点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差别。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写于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动摇了他们以及很多德国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启蒙观念的合法性[23]P127-132;对理性、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坚信[24]P35-38,被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绝望情绪所替代。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他们认为,不仅大众没有任何主体性可言,就是作为精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自身难保。与此不同的是,英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受到法西斯主义的重创,知识分子也没有受到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加上利维斯本人不是左派人士,因此他所看到的社会前景并没有那么的暗淡。尽管担忧大众文化的泛滥会使英国走向没落,尽管以缅怀过去作为聊以自慰的方式,但利维斯还是相信教育能够救国的信念,并利用他在英国教育界里两门大学课程——英语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力[15]P13,培养一帮能用笔杆子打击大众文化,推广高雅文化的弟子。因此在悲观情绪的背后,利维斯仍然为意志主义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留下了地盘。如果说,《启蒙辩证法》表达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文化精英主义,那么利维斯主义就是一种带有乐观主义悲剧意识[25]P9-15的文化精英主义。其次,从政治立场上看,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激进人士,批判大众文化意在超越资本主义,而利维斯属于保守人士,批判大众文化意在回到封建社会,因此同样是文化精英主义,却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区分。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两种立场背后所指向的阶级利益显然是不同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也随之建起,这为后人的选择和扬弃提供了契机。
四选择与导向:大众文化的观念重构
与英国社会的民主化对于利维斯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上述我们所区分的两种意义上的利维斯主义,因为两者是统一的。问题在于,利维斯坚持了一种老派的西欧精英论的文化标准,这种标准容不得大众生活方式作为“文化”而存在,因此,大众文化也不应该用“细察”的方法加以研究;不过,大众文化的强势来袭以及背后所隐含的美国文化霸权,又迫使他不得不认真面对,在藐视与重视之间,在近距离细察和远距离观望之间,利维斯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辩证空间:既然大众文化比少数人文化更强大,简单粗暴的对待大众文化显然结局悲惨,要想抵抗之,还得“细察”之,因此,两种意义上的利维斯主义需要分离。在这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尽管不愿意承认大众文化的合理性,但默认了它在语义上的合法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利维斯的文化标准逐渐变得过时而越来越私人化,这是对文化持总体性观点的后人所反对的,威廉斯将之命名为粗糙的“标准理论”(theoryofstandard)[26]P310,即以一种家长制的方式规定什么是文化,什么不是,它的反面则是将标准放到共同体所有成员之中去协商,不断地修改之,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发挥时代关键词的语义力量。因此,尽管当时的美国大众文化并不是完美的,但至少当时美国人的文化标准比西欧精英论的文化标准更具有民众性,因而也更具有民主的潜能,这与战后英国的社会阶级分化进程[27]P179-187有着某种契合性。所以,大众文化的命运,就跟战后英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文化研究的诞生变得非常重要。正是大众文化这样一个新事物的出现给当时的西欧精英界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于威廉斯所描述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包括利维斯主义者)①而言,这是工业主义对社会的新挑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则是资本主义以另一种方式焕发生机后对社会主义的新威胁。不过对威廉斯等人而言,利维斯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太悲观了[30]P63,这种悲观不仅仅是由阶级偏见和政治上的无助造成的,也有理论方面的困境,而根子就在于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矛盾态度上。因此,当时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②呼唤着一种能够更好地克服这些矛盾,解释这些新现象的总体性理论,这样就有了“文化转向”的社会期待。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在投身于战后成人教育运动[31]P24-25,介入大众文化批判领域后写出的文化研究“四大经典”——《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32]P31-40,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样一种需求。不过,威廉斯等人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肯定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而是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思考对象,比如霍加特对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生活方式进行亲知性地描述,意在为工人阶级争夺平等的话语权,捍卫工人阶级自主生活的权利;威廉斯探讨英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大众文化”,意在通过批判的方式肯定大众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通过日常生活这个媒介而推动着社会进步;而汤普森探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则意在揭示英国激进主义运动史背后的大众文化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存在于历史中,而且存在于当下,它使得人民能够借助它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摆脱家长制的束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共同体。[34]P13尽管三人对大众文化的切入点不同,但无疑指向同一个话题: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说,他们所探讨的大众文化已经不是指一种事物,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作为“整体生活方式”(awholewayoflife)的文化,③这种观念还有另一个表达法,即威廉斯所说的“选择性传统”(aselectivetradition),选择性传统意味着传统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而是可以拆解成不同要素并进行重新组合,因此,美国的大众文化在经过英国化之后,就可以成为英国人的民主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利用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技术为公众创造更多的表达心声的机会。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一部分,思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正是在对美国大众文化、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解构和重新组合上,文化主义部分选择了美国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众文化,降低了它的娱乐性和审美性;选择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总体性和利维斯主义的文化主体性观念,否定了他们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之整合进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里头,确立了英国式的大众文化话语。这使得英国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理论输出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美国的文化霸权,同时文化主义也抵御了英国的中产阶级文化霸权,实现了理论创新并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实践,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左派人士包括中国学者的尊敬。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主义的理论创新得益于这样一个时空契机: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象征美国霸权的大众文化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冲击着西欧社会,加速了西欧社会的阶级分化,造成了西欧精英阶层既轻视又恐惧的不服气心理,由于他们用的理论武器是西欧式的文化定义,因此对美国式文化的批判显得软弱无力;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批判尽管增强了这种批判力,却也因为沾染了西欧人的文化精英主义而走向悲观主义。不过,正是这两个学派共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理论空间、问题域,以及多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使得文化研究得以可能,加上威廉斯等人“识时务”地选择,使得大众文化批判朝向新的方向——文化研究而发生裂变。时隔半个多世纪,对于世界左派学界和中国学界而言,文化主义至今仍是有生命力的,因为他们坚持了一种历史选择和思想史选择的标准:在历史传统和思想史传统的解构和重构过程中,将阻碍人民说话、独立、自由的家长制因素去除,将民主的因素整合进传统,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策略,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原则。因此,回顾文化研究的史前史,让我们更深切地看到文化主义的魅力,也给予我们关于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和标准的启示。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201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