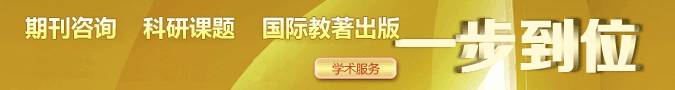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意义及发展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传统与主要问题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所含的最年轻学科。它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从两个方面延续而来。第一,西方所谓的“世界文学”,起源于歌德对“人类共同财产”的呼唤;由此他将“世界文学”区别于“民族文学”,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世界文学的时代……早日来临”。①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出发,提出“精神的生产”必然同“物质的生产”一样,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进而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按照朱光潜先生的说法,两种“世界文学”的含义似乎大致相同,只是分别基于“普遍人性”和“世界市场”的观点而已;③按照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Wellek)的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每个民族都在……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而并非“放弃它的个性”。④由此立论的“世界文学”,无论是对物质生产之决定性作用的判断,还是诗人式“普世主义”的理想,恰好都可以成为一种比较性研究的观念基础,却与中国高校学科建制中的“世界文学”相去甚远。从“世界文学”所曾经历的学科归属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指中国学人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而已,因此才一度被“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所排斥。如果不能在汉语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提供恰当定位,其学术身份就始终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第二,“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之说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后来形成了注重研究国际文学之间关系的法国学派,以及注重美学批评的美国学派。1954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后,各国比较文学学会也相继诞生,比如法国(1954)、日本(1954)、美国(1960)、德国(1968)、加拿大(1969)、菲律宾(1969)、匈牙利(1971);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则成立于1985年。自此不断有学者提及的所谓“中国学派”,也被逐渐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跨文化的东方立场、“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原则、借助外来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等等。①从“比较文学”的上述发展看,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的形成,都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同时又始终没有离开其文学或文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线索。因此,尽管西方大学建制中的“比较文学系”远远早于中国,却未必是什么“学科意识”的产物,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超越学科的研究平台,其基础则在于更为开放的文学视野。正如美国学者勃洛克(HaskellM.Block)为“比较文学”作出的定义:“在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时候,与其强调它的学科内容或者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如强调比较文学家的精神倾向。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②相对而言,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当其初始之时,也曾因其观念之新、方法之新而振聋发聩,并对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学术之复兴起到过重要作用。③但是,也许因为我们过于热衷“学科”和“学派”的建立,从而对“方法”本身及其“学科”独立性的关注日甚,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比较文学”的根本命意及其应当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整体启发。这样,一方面是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趋于萎缩,另一方面,勃洛克式的开放态度又引起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何以成为独立学科”的担忧。其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也许注定是关联性的,对中国学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种“倾向”、“前景”、“观点”或者“设想”,而且也表达着当代人文学术的内在精神;不仅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立身之本,也是文学研究之人文学价值的关键所在。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和内在精神
理解已经是诠释。在汉语的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定位,已经意味着一切外国文学研究都必然以“比较”的观念为前提。在汉语语境中,任何纯然的“×语语言文学研究”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谓,在这一意义上特别强烈地凸显出一种内在精神,其价值远远超越了那些学科之争。择其要者,至少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从“对话”到“间性”的意识
“对话”是“他者”的自然延续。“让他者成为他者”既是一般对话理论的基础,也正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起点。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所展开的“对话”,显然不是要在不同文学之间清谈什么“可比性”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借鉴“他者”的经验,或者论说所谓的文化多元。归根结底,“比较”中的“对话”最终是要返诸己身,透过一系列对话关系重新理解被这一关系所编织的自我。其中最基本的意义,是“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更充分地揭示自己”,从而“相互丰富”。①这应当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整体研究的独特价值。进而言之,“比较”与“对话”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当代人文学术从不同角度所关注的“自我的他者化”(self-othering)②、“对宾格之我的发现”(Me-consciousness)③,亦即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识。意识到“我”具有主格和宾格、指称者和被指称者的双重身份,意识到“主体”只是存在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对话”便成为起点而不是落点,“对话”也才能超越近乎托辞的“多元”,进入到“间性”的自省。其中所包含的自我批判,乃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断激活甚至重组人文学术的根本原因。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往往并不是停留在文学文本的比较和分析,而是对“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和现代性神话的全面颠覆。
(二)“问题”对“学科”的消解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的内在精神也会成就一定的表达形式,那么曾经作为知识表达形式的“学科”概念必然要受到“他者”、“宾格之我”和“间性”意识的深层影响。这些意识在学科制度中的渗透,注定要带来学科界限的消解和跨学科研究的形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本身,就格外突出地显示出一种“学科的间性”(inter-disciplinary),亦即“跨学科性”。“学科”之由来,其实只是为了回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活动。当曾经建构过某一学科的社会状况不复存在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该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被重组。在当代人文学术的研究领域中,学科界限的消解和学科专业的“问题化”趋向,或许正是当代社会对人文学术的最根本建构。这早已不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而是确凿的学术现实。作为一个最年轻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格外鲜明地反映着当代学术的“非学科化”倾向。因而大量的“普遍性论题”和“公共话语”,常常都是首先进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视野,同时又不能为任何一个学科所独有,也没有哪一个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所以可能成为学科重构的典型,正在于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的论题范围和研究领域。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曾经以学科方式回答过的种种问题,在20世纪以来又都成为了新的问题,并且是以非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式重新被提出。现代性进程一方面加速完成了“学科化”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对“学科化”的反思性怀疑和批判。④就此而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这一过程同步而且同构的。
(三)“弱势”和“边缘”的文化策略
沿着“他者”、“宾格之我”、“间性”及其对传统学科界限的消解,也许可以大致描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和内在精神。其中的逻辑线索集中体现了当代人文学术的基本处境,其中所蕴涵的先锋性和批判性也会再度回馈这一处境。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文学比较和文本分析的超越,一方面使它代表着一种知识方式的重构,另一方面也由此而成为弱势群体或边缘文化“改变世界”并“阅读自己的文本”⑤的直接手段。从这样的角度考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们会发现它所导致的阅读活动注定要延伸为一种“弱势”的立场。比如对文学文本的“历时性”考察,几乎必然会质疑“共时”的文化结构;“阅读自己的文本”,几乎必然会动摇“叙事”所编织的意义和秩序。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女性主义写作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既通过叙事主体和语境的变换为“比较”提供了理论支点,又恰好借助于“弱势的性别群体”和“弱势的边缘文化”向强势文化及其“话语霸权”发出了挑战。由此而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可以被表达为弱者的文化策略。这与“他者”的呈现、“间性”的意识及其对于“学科”的消解一样,最终的根基和意义未必只限于文学文本和文学阅读自身,而应当拥有更广阔的天地。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趋向及可能空间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曾有过相当迅速的发展,曾经聚集过文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科中一批最活跃的学者。然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张力、“学科意识”及其内在精神的冲突、理论旨趣和批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特别是较多存在于这一领域的“教材体”或程式化的写作方式,都日益明显地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使“大旗号”下的具体研究难以深入。就此,研究者相继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其中所蕴涵的,正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未来趋向及可能空间。
(一)“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视野
“比较文学”被界定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①,已经是学界的共识;而中国学人所能展开的“世界文学”研究,实际上也必然会分有“比较文学”的基本性质。但是这一性质的真正体现,显然不在于它能否保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独立地位,却在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潜在命意和人文学价值。换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人文学视野,是其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这必然与技术化、程式化的研究相互抵触,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被狭隘的“学科”归属所束缚。在近些年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逐渐被问讯的实际上正是一些更具人文学意味的问题。比如从“文学间的对话”到关于“存在”的对话性意识,从母题、形象或者类型的异同到关于文化想象与文化身份的结构性分析,从文学与文化范式的梳理到关于“经典化”(canonization)过程的揭示。也许可以说,这些都将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自然延伸。
(二)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史”视野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向,还将导致一种对于“外国文学史”的全新叙述。这一方面意味着“教材体”写作必然被抛弃,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史的研究必须被置于批评史的背景。西方学界借助不同批评方法处理同一文学作品的尝试,便是可循之例。比如在美国出版的“当代批评中的个案研究”丛书中,《哈姆雷特》之类的文学经典都是根据心理分析学派、英美新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典型的批评模式,得到多层面的读解和描述,②从而使文学理论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展开,文学史又被批评史的线索激活。长期以来的“学科规范”和“教材体”叙述方式,不仅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难以深入,实际上也早已引起学生的反感。不久前有学生在互联网上发表《〈机器猫〉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一文,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文科的刻薄和想象,运用那些充斥于外国文学教科书的典型术语和分析模式去“解读”日本人写给小孩子看的连环画《机器猫》,从而使这种“解读”显得非常可笑。而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觉得它可笑,只是因为被解读的文本并非“巨著”,也毫无崇高感可言,其实同样的解读方法大量存在于相关的“教材”、“研究”和“学术训练”之中。有鉴于此,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对“外国文学”进行重述,有理由成为我们的期待。
(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在目前的文艺理论界,“文化研究”确实引起了诸多争论。而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未来空间而言,它不仅注定是题中之意,而且可能会带来“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学科意识”远不及国人强烈的西方学界,这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争议。20世纪后期以来,在影响颇大的Polity出版公司“文学研究”网页上,“文学研究”(LiteraryStudies)已经同“文化理论”(CulturalTheory)合并为一类,并开列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理论前沿书目”(thecutting-edgelistofliterarystudiesandculturaltheory)。这种所谓“文化转向”的基本意图,是要突破狭窄的审美中心和文本中心,将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审美的思想文化领域和非文本的一切文化对象。因此,西方的传统文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通过历史文献的钩沉和文学文本的重读,与解析历史文化之成因、结构和趋向的“文化研究”相关联,其中一些问题日益成为整个人文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比如文学想象对文化身份的参与(Sex,LiteratureandCensorship,byJonathanDollimore)、语言结构对价值秩序的渗透(Language&SymbolicPower,byPierreBourdieu)、文本重读对历史叙述的质疑(OutsideintheTeachingMachine,byGayatriChakravortySpivak)、文学诠释对政治哲学的介入(HermeneuticsasPolitics,byStanleyRosen)、文学研究针对“全球化”潮流进行的反思(AnAnti-CapitalManifesto,byAlexCallinicos)、文学研究对“强势文化”的批判(CultureandImpe-rialism,byEdwardSaid)等等。如何评价上述趋向的最终结果,当然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或许应该承认:这一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正在超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自身,悄悄地影响着“中国语言文学”的整体学术品格。
本文html链接: http://www.istpei.com/qkh/19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