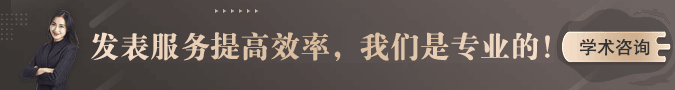白蛇传中的叙事学
2021-4-9 | 外国文学论文
一、学科定义与选题意义
经典叙事学是一门对叙述进行结构研究的科学,它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是在纷繁芜杂、种类庞多的叙事作品找寻具有普遍意义的组成要素。追本溯源,经典叙事学就是从对叙事性文本的结构性分析中发现叙事的普遍特征,探寻其结构规律。这种彰显于叙事学定义之中的结构主义的特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更为经典叙事学于20世纪80年代的没落埋下了理论根基上的隐患。《白蛇传》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与普罗普的俄国民间故事、布雷蒙的法国神话传说相比,更为国人所熟知。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无疑体现的是东方式的叙事哲学。经典叙事学这一根植于西方的理论成果能否成功地阐释这一东方传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基于《白蛇传》的叙事学角度分析与比较,将会为我们看待经典叙事学的成就与桎梏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和切近的依据。
二、普罗普与“叙事功能”
完成于1928年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在问世后的30年中一直籍籍无名、乏人问津,直至上世纪60年代英译本问世,普罗普及其著作才在法国叙事学界声名鹊起。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将俄国的各种童话集中起来作了全面考察,从中概括出他称作“功能”的31种构成因素,然后将之组合到七种角色的“行为范围”中,详细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出了一套结构程式。尽管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民间故事的形态学》并没有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涤荡和洗礼,但其中体现的理论思想明显体现了结构主义寻求有限的、本质的、深层结构的基本观点。普罗普在归纳其创作动机时提出:“要以最小的篇幅涵盖最大限度的内容,……就类似于一种语法。”(罗钢,1995:26)利用普罗普的分类,我们可以轻易地把《白蛇传》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如此,流传在民间一波三折情节跌宕的白蛇传被转化成了一串数字与符号。这样的转化证明了普罗普31种叙事功能在跨越了东西方的差异之后仍具备可操作性,然而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白蛇传》为例,情节3与情节4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从情节8与情节9有无空间的转换?是什么在连接这些字母与符号?这些符号间是否反映逻辑?如果选择的文本并非民间叙事文学,则他的分类是否可以行得通?对于这些问题普罗普均没有给出正面的解释。所以他的研究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研究,它只重故事表层的句法关系而不重深层的逻辑关系,它是一种时间静态的堆叠而不是动态的描述,连接各个符号之间的只是简单的时间关系而缺乏空间关系和逻辑结构。
三、布雷蒙与“叙事逻辑”
尽管布雷蒙对普罗普叙事功能的提出深以为然,然而他敏锐地意识到没有逻辑连接的叙事功能就如同没有黏合剂的砖瓦,由此砌成的大厦倒塌只是时间问题。故此,他提出了“叙事序列”的观念作为叙事的基本单位,希图以此解释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叙事的基本序列由三个紧密相连的功能组成,即情况形成—采取行动—达到目的。继而对基本序列进行变化和组合,使其更为适应多样的叙事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布雷蒙的叙事序列与前人普罗普相比更具逻辑优势。由于时间发展是由内在逻辑推动的,情节之间就不再是简单时间顺序的排列。他又给予这种逻辑充分的弹性空间,在每个功能项下,都存在着改善或是恶化、成功或是失败的可能。许仙可以借伞也可以不借,白素贞对许仙的倾慕可以实现也可以失败,许仙不一定遇到法海,法海也不一定认出白素贞是妖怪。所以布雷蒙的理论事实上是强调事件发生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产物。其理论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和改进了普罗普的叙事功能理论,更在于通过展示故事的推进方向很大程度是人物的选择凸显人物的意志力量。他所着眼的逻辑,本质上是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尽管他没有把读者、作者考量在内,但毕竟承认了人物对于情节的关键作用,为强调客观、科学的早期经典叙事学研究增添了一份对人的关注。
四、格雷马斯与“语义方阵”
同是从普罗普的叙事功能出发,格雷马斯选取了一条与布雷蒙不同的叙事学研究之路。他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是“文本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格雷马斯对意义的关切使得他把眼光投向索绪尔和斯特劳斯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故此,格雷马斯锁定结构语言学为基本模式、决心以寻找和归纳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来推导叙事模式。把这些角色和逻辑秩序带入语义方阵,我们得到的便是一种深层逻辑结构。与普罗普的图式相比,格雷马斯的图式当然更具有逻辑性、更富于概括力,也更宏观、更抽象。格雷马斯所提出的情节秩序意味着叙事的意义和基本框架已经在作者脑中预先搭建,譬如作者在创作《白蛇传》故事之初就已经有了一个预设好的深层框架,他只不过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和填充这个框架。那么对于读者而言,理解这一叙事就首先必须跨越自我的思维间架结构。这就要求读者既对作者的预先的叙事的模式熟悉和认同,又准确地解读作者叙事模式的内在含义。这样势必就会带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抗,从理解再到沟通与认同。但同时,只有在读者参与的状态下,叙事的确定权才真正交付给读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格雷马斯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了读者的作用,这无疑暗合了新叙事学或后经典叙事学。
五、托多洛夫与“叙事句法”
托多洛夫的理论是从一个简单的类比开始的。与格雷马斯同为符号学家,托多洛夫也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符号,语言是符号的集合,那么叙事也不例外。既然在语言世界存在着一种基本语法,叙事中也必然存在叙事语法。于是文学和语言在托多洛夫是异质同构的两个系统,而包括叙事在内的文学是语言某种属性的拓展和应用。于是,托多洛夫另辟蹊径,致力于参照语言学的模式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则,建构一套新的叙事结构模式。在他看来,一个单一的句子就是一篇简单的叙事文本;而复杂的叙事文本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托多洛夫认为,从“一个平衡向另一个平衡过渡,就构成了一个最小的完整情节”,是故事的最基本的结构程式。尽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切入方式,但托多洛夫的研究展现出了与前人高度的相似性。当然,在分析如《白蛇传》的民间故事时托多洛夫的理论充分显示出其可操作性,然而简单化的故事民间情节和主角/破坏者的角色分类使他们的研究成果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尽管他们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发现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解释一切的叙事内容,而结果是,他们得到的结论其实并不能解释大多数叙事文学作品,遑论指导文艺创作。
- 今日更新
-
- 出版国际著作 想快速出版的来看
- 论文怎么发scopus收录期刊
- 国内认可scopus检索论文吗
- SCOPUS收录检索论文领域
- 语言学论文发scopus期刊
- sci期刊撤回论文有影响么
- 写论文需要写前言吗
- SCI三区期刊好发表论文吗
- 论文录用通知交版面费
- 如何知道出版社出书多少钱
- 挑选发表论文容易通过的SCI期刊技巧
- 《安徽医药》期刊发表论文情况分析
- 论文附录是什么?放在什么位置
- SCI期刊查找论文格式指导及投稿格式重要性
- 通信领域的英文期刊含sci
- 了解sci/ssci期刊发表论文费用的4个方法(含官方报价)
- WoS数据库认识与检索论文、期刊的攻略
- 医学卫生系列职称论文4个实用软件
- MDPI 会议|国际农业电子会议开放征稿
- 又1本国产期刊被EI收录《Data Science and Management》数据科学领域期刊